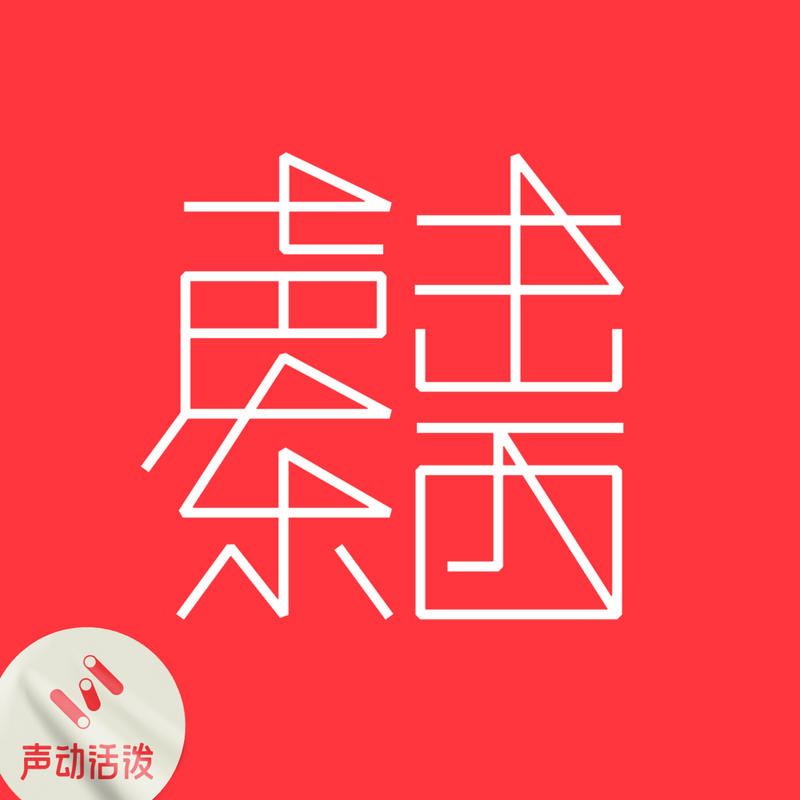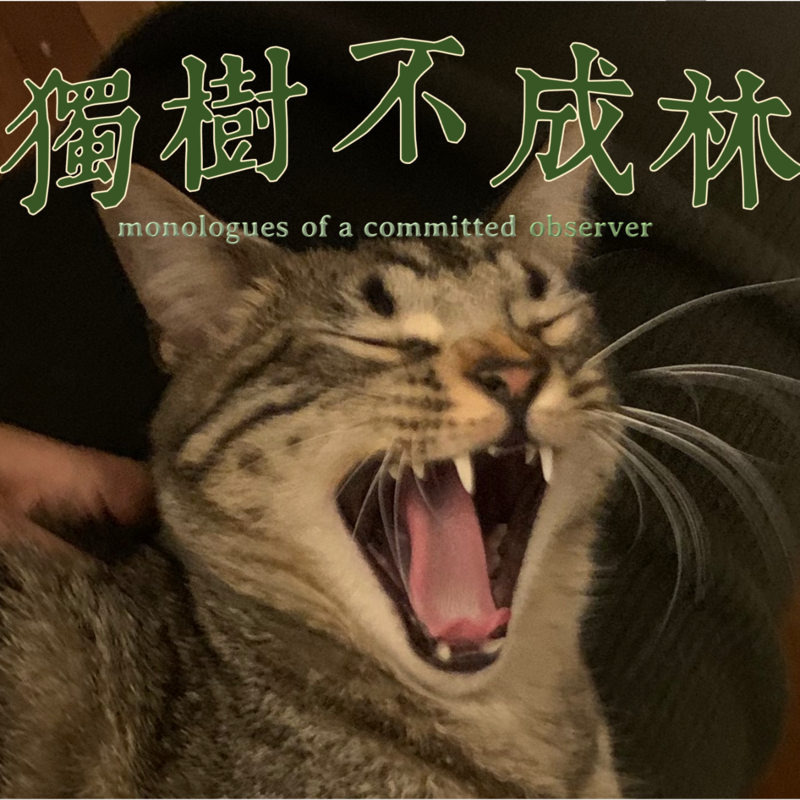cake and
像好朋友一样说话

主播:
cake是只猫、And and
出版方:
cake是一只猫
订阅数:
7,170
集数:
30
最近更新:
4周前
播客简介...
cake(❍ᴥ❍ʋ):像好朋友一样说话!都是随机波动!一样爱发疯就一起来听来玩!!
and(¯―¯٥):神经病。。。但是真的好开心!
漫谈在不太严肃和太不严肃之间高频震荡,题材任性,希望喜欢:)
cake and的创作者...
cake and的节目...
cake and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