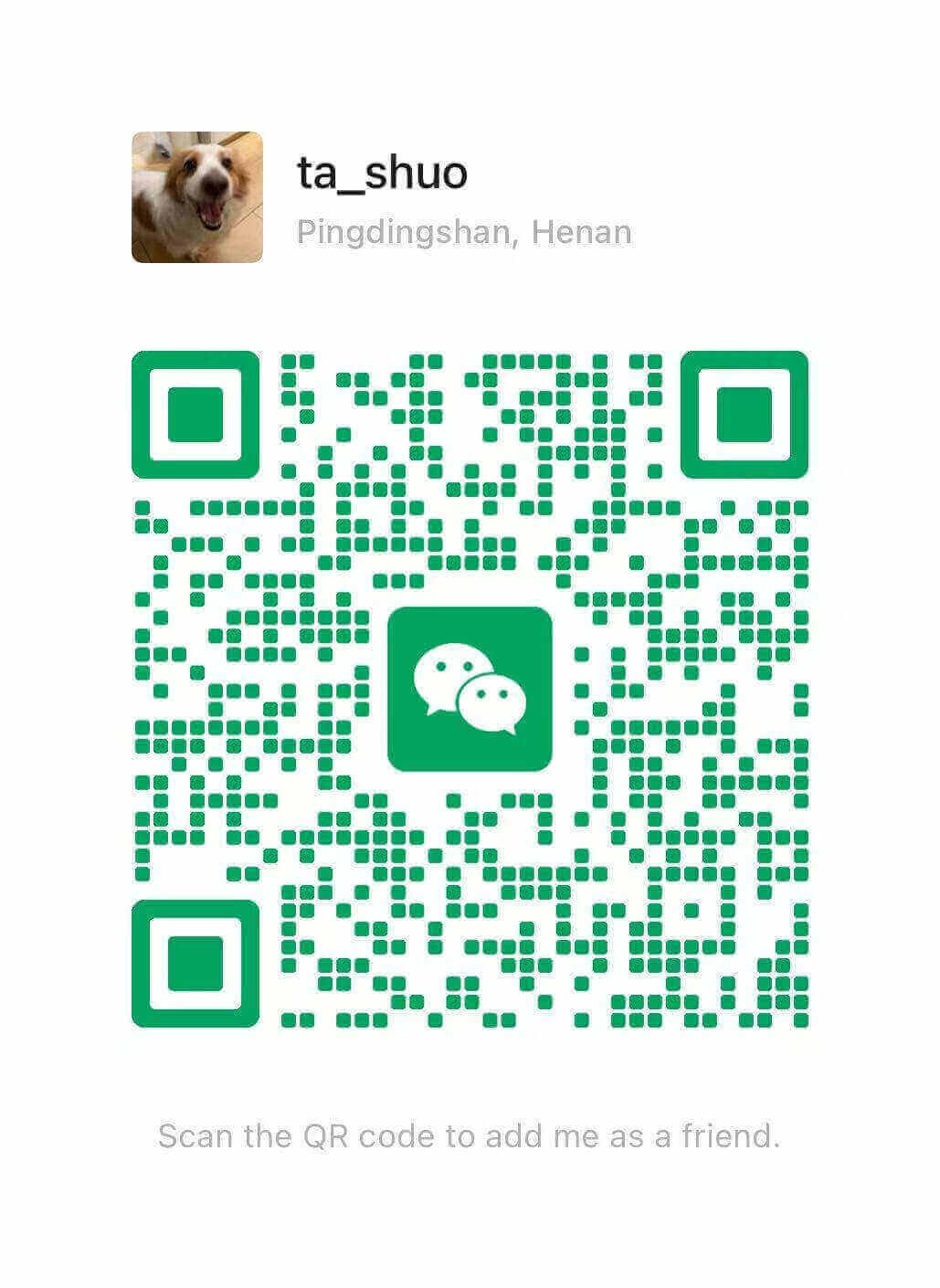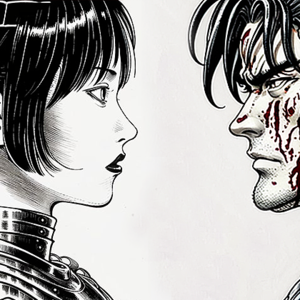
时长:
15分钟
播放:
2,804
发布:
3个月前
主播...
简介...
这些日子以来,我的认知改变极大,虽然这一过程两个月前就开始了。我明确感受到自己被“抬旗”了。但我感受到巨大的失重感——不是兴奋,也不再是激情了。
这种感觉很怪。就像我现在经常在想:我过去生活的这许多年里,究竟在干什么?
我过去常年来习惯在一个现成的、有明确规则的系统内活动。我对世界的认知模式说白了仅仅来源于“如何更好地适应和利用现有规则”,完全是一种应用层面的优化。
而现在,我天天看到的不再是“如何在现有规则里更好地活着”,而是 “规则是如何被设计和改变的” 。
我看到过去的自己如此低贱与卑微,却以为曾经的我是自由的,是快乐的,是激情燃烧的。我以为那样的我,就是足够完满的状态。
我感受到巨大的认知差异和人生状态的根本性不同,我过去竟然用如此简单粗鄙的方式去理解自己作为复杂个体的社会化状态,我对我的曾经头晕目眩恶心想吐,我的感受大约就是——惶恐。
愚蠢的我,过去总认为“踏实工作”是美德。但现在我看到,一个决策的价值远超普通人一生的勤恳。所以,何为价值?何为努力?而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我会是谁?我终极的模样是什么样的?
这就不是性别的问题了,这是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一旦不指向性别,就会指向最痛苦的领域——存在。
过去我的责任是“对任务负责”“对岗位负责”。现在的责任是 “对全局负责”“对结果负责” ,甚至大部分时候是“对跟随我的人的命运负责”,这里包括我的整个内部家庭和外部团队。
这种“区别”,不是量的差距,是维度的不同。
“趋势是什么?”“规则为何这样设定?”“我如何成为设局者?”
我的消费习惯没有改变,但认知已翻天覆地。我必须将曾经的亲人、朋友、战友、情感纳入制衡框架中去审视。我需要剥共情和信任,代之以绝对的理性和怀疑,不断训练我的极端理性。
我不得不彻底抛弃寻找单一社会标签来定义自己的渴望,转而接受自己是永恒冲突的多核的联合体。我变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的责任是抽象的、系统的、且后果不可逆的。
我慢慢发现,系统的责任意味着没有标准答案,且每一个决策都充满未知风险。我无法再通过完成任务来获得安全感,必须在不确定性中独自做出判断。
我必须从执行者的心态,彻底转变为创始人和船长的心态。我得习惯于日复一日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依靠直觉和魄力做出决策,并为所有后果承担终极责任。
没有人再会明确地告诉我怎么办。没有人。
————————————
写到这里,我必须自己写出答案:
面对以上彻底转变,我需要刻意修炼三种能力:
极高的情绪张力:能在不同身份和价值体系中快速切换,而不产生内耗。这需要像训练肌肉一样训练情绪。
强大的系统思维:能看清复杂系统中各要素的关联,并能预见决策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深刻的哲学自省:需要建立一套自洽的、强大的内部哲学体系,用来解释和指导自己的行为,抵御外界的道德评判,并安抚自己内心的波动。
我要继续训练自己的灵魂核心。过去我这么做是为了活着,现在我这么做是为了存在。
这种感觉很怪。就像我现在经常在想:我过去生活的这许多年里,究竟在干什么?
我过去常年来习惯在一个现成的、有明确规则的系统内活动。我对世界的认知模式说白了仅仅来源于“如何更好地适应和利用现有规则”,完全是一种应用层面的优化。
而现在,我天天看到的不再是“如何在现有规则里更好地活着”,而是 “规则是如何被设计和改变的” 。
我看到过去的自己如此低贱与卑微,却以为曾经的我是自由的,是快乐的,是激情燃烧的。我以为那样的我,就是足够完满的状态。
我感受到巨大的认知差异和人生状态的根本性不同,我过去竟然用如此简单粗鄙的方式去理解自己作为复杂个体的社会化状态,我对我的曾经头晕目眩恶心想吐,我的感受大约就是——惶恐。
愚蠢的我,过去总认为“踏实工作”是美德。但现在我看到,一个决策的价值远超普通人一生的勤恳。所以,何为价值?何为努力?而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我会是谁?我终极的模样是什么样的?
这就不是性别的问题了,这是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一旦不指向性别,就会指向最痛苦的领域——存在。
过去我的责任是“对任务负责”“对岗位负责”。现在的责任是 “对全局负责”“对结果负责” ,甚至大部分时候是“对跟随我的人的命运负责”,这里包括我的整个内部家庭和外部团队。
这种“区别”,不是量的差距,是维度的不同。
“趋势是什么?”“规则为何这样设定?”“我如何成为设局者?”
我的消费习惯没有改变,但认知已翻天覆地。我必须将曾经的亲人、朋友、战友、情感纳入制衡框架中去审视。我需要剥共情和信任,代之以绝对的理性和怀疑,不断训练我的极端理性。
我不得不彻底抛弃寻找单一社会标签来定义自己的渴望,转而接受自己是永恒冲突的多核的联合体。我变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的责任是抽象的、系统的、且后果不可逆的。
我慢慢发现,系统的责任意味着没有标准答案,且每一个决策都充满未知风险。我无法再通过完成任务来获得安全感,必须在不确定性中独自做出判断。
我必须从执行者的心态,彻底转变为创始人和船长的心态。我得习惯于日复一日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依靠直觉和魄力做出决策,并为所有后果承担终极责任。
没有人再会明确地告诉我怎么办。没有人。
————————————
写到这里,我必须自己写出答案:
面对以上彻底转变,我需要刻意修炼三种能力:
极高的情绪张力:能在不同身份和价值体系中快速切换,而不产生内耗。这需要像训练肌肉一样训练情绪。
强大的系统思维:能看清复杂系统中各要素的关联,并能预见决策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深刻的哲学自省:需要建立一套自洽的、强大的内部哲学体系,用来解释和指导自己的行为,抵御外界的道德评判,并安抚自己内心的波动。
我要继续训练自己的灵魂核心。过去我这么做是为了活着,现在我这么做是为了存在。
评价...
空空如也
小宇宙热门评论...

素食者_
2个月前
湖北
5
非常非常恰逢其时的一期播客。我和舒蕙老师有着几乎完全相似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所谓qs100毕业博士生找到不太理想学校的教职,再加上对于育儿的挣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看不到光的生活。然而在经历了关于生育与身体的一系列阅读和生活体悟之后,我开始由衷地被“我可以看见他人”这件事治愈。舒蕙老师这里用的概念是角色,但我更希望用“主体间性”来形容这种感觉,是一种因为你能看见、回应并满足他人的需求所形成的安全感。所有的性别也好等级也好的划分变得不重要了,那些纠结也感觉都散开了。在之前我非常痛恨身边的所有人,我的丈夫、我的婆婆,我看到的是他们作为结构中的一员给我施加的不公,这种感觉让我很痛苦。但现在我觉得他们或许真的看见了我并在尝试帮助我。或许这样的分工仍然在复制某种不公,但我好像跳脱认知上的禁锢,获得某种实践上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我们互相“看见”,并即时地体验那些真实涌动的情感。或许这是某种“开悟”吧。

粤北
1个月前
美国
3
华人世界的这种“自我”,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悬置状态:
它已经从传统的“宗族/集体”中挣脱了出来,切断了向下的根(不需要为了祖宗活);但它还没有建立起向上的、或者横向的超越性连接(没有为了真理、信仰或公共善而活)。
它孤零零地悬在半空,除了“保卫自己”之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意义。
在这种状态下,“爱”变得极其困难。因为爱(无论是对上帝、对真理、还是对孩子)本质上都需要让渡一部分主权,都需要一种“自我消融”的勇气。而对于一个处于“报复性保卫战”中的自我来说,这种让渡等同于自杀。
所以,并不是这代人自私,而是他们的“自我”太脆弱了。一个随时觉得自己要被环境吞噬的人,是不敢敞开怀抱去拥抱另一个生命的。

粤北
1个月前
美国
3
华人世界的这种“自我”,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悬置状态:
它已经从传统的“宗族/集体”中挣脱了出来,切断了向下的根(不需要为了祖宗活);但它还没有建立起向上的、或者横向的超越性连接(没有为了真理、信仰或公共善而活)。
它孤零零地悬在半空,除了“保卫自己”之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意义。
在这种状态下,“爱”变得极其困难。因为爱(无论是对上帝、对真理、还是对孩子)本质上都需要让渡一部分主权,都需要一种“自我消融”的勇气。而对于一个处于“报复性保卫战”中的自我来说,这种让渡等同于自杀。
所以,并不是这代人自私,而是他们的“自我”太脆弱了。一个随时觉得自己要被环境吞噬的人,是不敢敞开怀抱去拥抱另一个生命的。

素食者_
2个月前
湖北
3
非常非常恰逢其时的一期播客。我和舒蕙老师有着几乎完全相似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所谓qs100毕业博士生找到不太理想学校的教职,再加上对于育儿的挣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看不到光的生活。然而在经历了关于生育与身体的一系列阅读和生活体悟之后,我开始由衷地被“我可以看见他人”这件事治愈。舒蕙老师这里用的概念是角色,但我更希望用“主体间性”来形容这种感觉,是一种因为你能看见、回应并满足他人的需求所形成的安全感。所有的性别也好等级也好的划分变得不重要了,那些纠结也感觉都散开了。在之前我非常痛恨身边的所有人,我的丈夫、我的婆婆,我看到的是他们作为结构中的一员给我施加的不公,这种感觉让我很痛苦。但现在我觉得他们或许真的看见了我并在尝试帮助我。或许这样的分工仍然在复制某种不公,但我好像跳脱认知上的禁锢,获得某种实践上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我们互相“看见”,并即时地体验那些真实涌动的情感。或许这是某种“开悟”吧。

素食者_
2个月前
湖北
3
非常非常恰逢其时的一期播客。我和舒蕙老师有着几乎完全相似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所谓qs100毕业博士生找到不太理想学校的教职,再加上对于育儿的挣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看不到光的生活。然而在经历了关于生育与身体的一系列阅读和生活体悟之后,我开始由衷地被“我可以看见他人”这件事治愈。舒蕙老师这里用的概念是角色,但我更希望用“主体间性”来形容这种感觉,是一种因为你能看见、回应并满足他人的需求所形成的安全感。所有的性别也好等级也好的划分变得不重要了,那些纠结也感觉都散开了。在之前我非常痛恨身边的所有人,我的丈夫、我的婆婆,我看到的是他们作为结构中的一员给我施加的不公,这种感觉让我很痛苦。但现在我觉得他们或许真的看见了我并在尝试帮助我。或许这样的分工仍然在复制某种不公,但我好像跳脱认知上的禁锢,获得某种实践上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我们互相“看见”,并即时地体验那些真实涌动的情感。或许这是某种“开悟”吧。

粤北
1个月前
美国
1
我觉得华人世界里“自我”这个主题还没有探索清楚。前一代人是强行被宏大叙事压抑,所以没有自我,那么后一代人就要报复式反弹,我偏要自我,我只要自我,执着到“他者”都消失不见了。这个时候生孩子就会有巨大障碍,因为孩子就不是属己之物,孩子是真“他者”。这个他者一出现,这代人好不容易通过报复获得的自我就受到了威胁,而这绝对不允许。孩子和自我之间出现了你死我活的关系。

粤北
1个月前
美国
1
我觉得华人世界里“自我”这个主题还没有探索清楚。前一代人是强行被宏大叙事压抑,所以没有自我,那么后一代人就要报复式反弹,我偏要自我,我只要自我,执着到“他者”都消失不见了。这个时候生孩子就会有巨大障碍,因为孩子就不是属己之物,孩子是真“他者”。这个他者一出现,这代人好不容易通过报复获得的自我就受到了威胁,而这绝对不允许。孩子和自我之间出现了你死我活的关系。

粤北
1个月前
美国
1
华人世界的这种“自我”,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悬置状态:
它已经从传统的“宗族/集体”中挣脱了出来,切断了向下的根(不需要为了祖宗活);但它还没有建立起向上的、或者横向的超越性连接(没有为了真理、信仰或公共善而活)。
它孤零零地悬在半空,除了“保卫自己”之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意义。
在这种状态下,“爱”变得极其困难。因为爱(无论是对上帝、对真理、还是对孩子)本质上都需要让渡一部分主权,都需要一种“自我消融”的勇气。而对于一个处于“报复性保卫战”中的自我来说,这种让渡等同于自杀。
所以,并不是这代人自私,而是他们的“自我”太脆弱了。一个随时觉得自己要被环境吞噬的人,是不敢敞开怀抱去拥抱另一个生命的。

素食者_
2个月前
湖北
1
非常非常恰逢其时的一期播客。我和舒蕙老师有着几乎完全相似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所谓qs100毕业博士生找到不太理想学校的教职,再加上对于育儿的挣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看不到光的生活。然而在经历了关于生育与身体的一系列阅读和生活体悟之后,我开始由衷地被“我可以看见他人”这件事治愈。舒蕙老师这里用的概念是角色,但我更希望用“主体间性”来形容这种感觉,是一种因为你能看见、回应并满足他人的需求所形成的安全感。所有的性别也好等级也好的划分变得不重要了,那些纠结也感觉都散开了。在之前我非常痛恨身边的所有人,我的丈夫、我的婆婆,我看到的是他们作为结构中的一员给我施加的不公,这种感觉让我很痛苦。但现在我觉得他们或许真的看见了我并在尝试帮助我。或许这样的分工仍然在复制某种不公,但我好像跳脱认知上的禁锢,获得某种实践上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我们互相“看见”,并即时地体验那些真实涌动的情感。或许这是某种“开悟”吧。

素食者_
2个月前
湖北
1
非常非常恰逢其时的一期播客。我和舒蕙老师有着几乎完全相似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所谓qs100毕业博士生找到不太理想学校的教职,再加上对于育儿的挣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看不到光的生活。然而在经历了关于生育与身体的一系列阅读和生活体悟之后,我开始由衷地被“我可以看见他人”这件事治愈。舒蕙老师这里用的概念是角色,但我更希望用“主体间性”来形容这种感觉,是一种因为你能看见、回应并满足他人的需求所形成的安全感。所有的性别也好等级也好的划分变得不重要了,那些纠结也感觉都散开了。在之前我非常痛恨身边的所有人,我的丈夫、我的婆婆,我看到的是他们作为结构中的一员给我施加的不公,这种感觉让我很痛苦。但现在我觉得他们或许真的看见了我并在尝试帮助我。或许这样的分工仍然在复制某种不公,但我好像跳脱认知上的禁锢,获得某种实践上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我们互相“看见”,并即时地体验那些真实涌动的情感。或许这是某种“开悟”吧。

素食者_
2个月前
湖北
1
非常非常恰逢其时的一期播客。我和舒蕙老师有着几乎完全相似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所谓qs100毕业博士生找到不太理想学校的教职,再加上对于育儿的挣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看不到光的生活。然而在经历了关于生育与身体的一系列阅读和生活体悟之后,我开始由衷地被“我可以看见他人”这件事治愈。舒蕙老师这里用的概念是角色,但我更希望用“主体间性”来形容这种感觉,是一种因为你能看见、回应并满足他人的需求所形成的安全感。所有的性别也好等级也好的划分变得不重要了,那些纠结也感觉都散开了。在之前我非常痛恨身边的所有人,我的丈夫、我的婆婆,我看到的是他们作为结构中的一员给我施加的不公,这种感觉让我很痛苦。但现在我觉得他们或许真的看见了我并在尝试帮助我。或许这样的分工仍然在复制某种不公,但我好像跳脱认知上的禁锢,获得某种实践上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我们互相“看见”,并即时地体验那些真实涌动的情感。或许这是某种“开悟”吧。

叫我张不会
1个月前
广东
0
第一次听,为什么会对女性身份厌恶?有什么故事吗

支起小耳朵
1个月前
河南
0
果然,大家的课题太不一样了。
1、一直是利他性的人,所以跟身边人相处,总是会下意识地去共情别人,甚至需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太圣母心,不要因为心疼别人而忽略自己的利益。
2、关于性别。体会到女性的难处,反而更加喜欢女性这个身份,因为她包容、拥有强大的同理心,感情丰富且无私,是比男性更伟大的存在。
3、关于孩子、母亲身份。一直以来都认为母亲身份只是一个幼小生命的养育者,和父亲、老师、甚至福利院院长没什么不同,只是一个幼小生命的引路人。

Cl3ment
1个月前
广东
0
小红书账号搜索什么呀

叫我张不会
1个月前
广东
0
第一次听,为什么会对女性身份厌恶?有什么故事吗

Cl3ment
1个月前
广东
0
小红书账号搜索什么呀

粤北
1个月前
美国
0
我觉得华人世界里“自我”这个主题还没有探索清楚。前一代人是强行被宏大叙事压抑,所以没有自我,那么后一代人就要报复式反弹,我偏要自我,我只要自我,执着到“他者”都消失不见了。这个时候生孩子就会有巨大障碍,因为孩子就不是属己之物,孩子是真“他者”。这个他者一出现,这代人好不容易通过报复获得的自我就受到了威胁,而这绝对不允许。孩子和自我之间出现了你死我活的关系。

Cl3ment
1个月前
广东
0
小红书账号搜索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