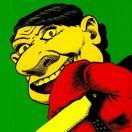Gene Pitney 吉恩·皮特尼
1940年2月17日——2006年4月5日
1960年,正在康涅狄格大学攻读电子工程的吉恩·皮特尼,在音乐和学业上艰难抉择,最后写下了一行字:“如果数学不能解爱情的难题,那就用三个八度高音炸开它!”,这个怪咖就此投笔从音乐,抱起吉他开启了乐坛最矛盾的职业生涯:用一副介于天使号角与玻璃碎片之间的嗓子,在60年代流行乐坛横空出世,他是百老汇的聚光灯,也是摇滚乐的荷尔蒙。
吉恩·皮特尼以词曲创作者的身份进入歌坛,当年他写给鲍比维(Bobby Vee)老师的《橡皮球》(Rubber Ball)登顶Billboard榜榜首,第二年,1961年,他包办词曲演唱,发行首支单曲《我想要与你共度此生》(I Wanna Love My Life Away),Billboard榜进入前40。能写能唱,这个就是睥睨众生的实力。1961年当年,他被制作人要求为冷战电影《暴雨狂云》(Town Without Pity)创作“能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主题曲”,他写出了《没有怜悯的城市》(Town Without Pity),前奏如同空袭的防空警报,声带化作在铁丝网上挣扎的云雀,歌曲获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提名:出道即巅峰,明日犹可待。
总是把西装扣扣到最上面一颗的绅士吉恩·皮特尼,也是60年代最危险的音乐风格走私客。他在《你好楼玛丽》(Hello Mary Lou)里把乡村乐浇上摇滚乐的汽油(这首歌被Ricky Nelson演唱,是他的经典之作,另外我个人觉得也是影响了《外婆的澎湖湾》)。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叫做《我要坚强》(I'm Gonna Be Strong),当别人还在纠结该讨好流行榜还是乡村榜时,吉恩直接把哭腔和歌剧唱腔集合在了一起,这个理工男的嗓音简直就是音乐界的量子纠缠——当这个刀片般锋利的高音切开《每一次呼吸》(Every Breath I Take)的副歌时,我实在是分不清那究竟是天使的圣咏还是恶魔的蛊惑。
吉恩·皮特尼的高光时刻是披头士滚石开始带着英伦音乐入侵美国时,他反向操作征服英国——1963年,他把滚石乐队两位大神的未发行歌曲《我唯一的女孩》(My Only Girl),改了旋律保留了歌词,变成了一首新歌属于昨天的女孩《That Girl Belongs to Yesterday》在大不列颠成功入榜,成为首位同时打入英美榜单前十位的美国人。
70年代以后,因为音乐风格的缘故,吉恩·皮特尼未能延续自己的神话,我个人把这归结于个人在时代的局限性,但他始终还是在延续自己的音乐事业,适应音乐行业的变化,从转向乡村和欧洲市场,到保持巡演和录音,也有单曲在80年代末登上单曲榜冠军。2006年4月5日,吉恩·皮特尼在威尔士卡迪夫的音乐会后台猝逝。工作人员发现他时,他穿着演出西装,乐谱上画满了修改符号。而今,当我们在音乐平台点开吉恩·皮特尼的歌单,我要请你调高音量,那些曾被诟病“过度戏剧化”的颤音,正在这个时代冷冷发笑——在短视频短平快的轰炸中,我们还是需要一个人,在时代的大潮中逆流而行,给你一点不一样的感觉。正如皮特尼老师在《最后转身的机会Last Chance to Turn Around》里唱的“当世界急着给一切打标签时,混乱,才是最高级的美学。”
本期选曲
If I Didn't Have A Dime
Town Without Pity
I'm Gonna Be Strong
Every Breath I Take
That Girl Belongs to Yesterday
Last Chance to Turn Around
空空如也
暂无小宇宙热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