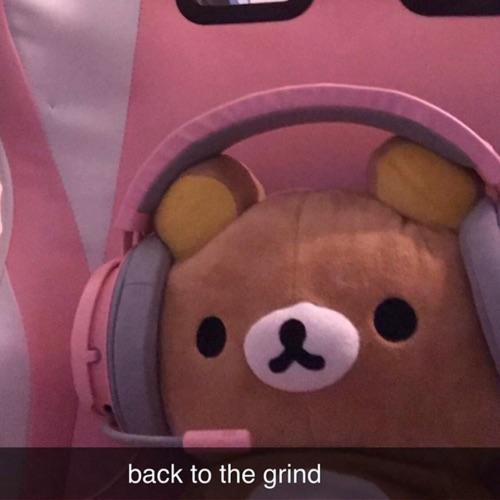如果是熟悉我此前在知乎活跃时期的写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并不喜欢朝夕光年,但是无论是在年前传出朝夕光年解散的消息之后,还是在上周五字节宣称重整游戏业务(与其说是重整不如说是收缩)之后,我的态度都是一致的:做事的人,大体是无辜的,而字节在游戏领域的撤退,确实也是让不少从业者失去了一些选择。
不过,过去一周行业里最流行的meme,恐怕就是“严授哭了三次”这个梗——只要你在任何一个聚集着游戏行业的讨论群或者饭局上,那你一定看过这个故事。正好就此延伸一点,水一期内容。
朝夕光年当然已经失败了,从很大程度上当然是战略的摇摆不定,而这种摇摆不定的背后,则是领导力和执行力的不足。但这个领导力不足的锅,严授要背,但恐怕不能全背。
严时代的字节游戏从2019年开始,恰好在游戏行业第一次版号寒冬结束后,不少游戏重新迈入收入轨道的时间点。
在严管理字节游戏业务之前,这个业务就是出名的烧钱黑洞:早期字节游戏的管理由新浪游戏出身,这段时间的业务的发展方向本身就混乱不堪,这段时间留下来最出名的项目,只剩下了杨中平的《三日战争》(当然这个项目本身故事更多)。
在游戏业务之前,严是字节战略部的负责人,但实际上更多是张一鸣的助理状态。他是跟随着今日头条业务发展起来的亲信,在字节决定发展游戏业务之后,严一直是一个代管,或者说在游戏业务中执行张一鸣意志的状态。
字节的游戏业务新创,为了能迅速把这个业务能够做到一定的体量。字节选择的道路是收购现有产能/成熟团队。而收购和团队磨合本身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尤其考虑到字节收购和吸纳的的实际上,都是一些颇具早期游戏圈江湖气的团队/公司,这里的问题就更大了。据说,在19年的时候,就有商务一个月在KTV豪掷百万并提请报销的事情。
在这种背景下,那么实际上严真正的任务是在于管好钱的流向,或者更直白说,是作为张一鸣能够信任的人,去管理字节准备投入游戏赛道的资源。而考虑到这点之后,去纠结字节游戏业务是不是应该严去背锅就意义不大了:按照朝夕全盛时期的架构,真正应该对游戏产品负责的,实际上是各个核心工作室的老板。
而在这个问题上,严本人的战略出身实际上就造成了很严重的局限性:无论是早期在咨询和腾讯SD,还是在张一鸣身边的工作,他本人去带一个需要”打仗“的业务的情况是很少的;而咨询出身又让他更倾向于信任战略给出来的判断。但如我一直以来说的,战略能起到的始终是信息提供,打辅助的作用,这种信任甚至盲信,决策权的上收,下面本应真正做决策的工作室head们只需要把“懒政”就可以甩很多锅出去了,若不是市场21年年中之后突然变差,只需要汇报搞好点,就高枕无忧。
汇报优先,导致的就是向上管理成为重中之重——在字节游戏这几年里,很多时候发生的与其说是向上管理,不如说是集体向上骗。
我听到最离谱的故事,就是字节上海将总部刻意设在张江(没有搬),这导致每次严去巡查业务的时候,都需要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种“疲老板之计”,极大地提高了忽悠的成功率。而类似离谱的欺上瞒下故事,也不是孤例。
每次听到这类八卦的时候,我想到的都是一本小说里看到的比喻,严实际上也如同“一个从未见过车、也没有开过车的年轻人,被赶鸭子上架去开一辆超重的卡车爬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很大程度上,他更合适的位置,还是当张一鸣的智囊团团长,而不是去趟这种业务的浑水。
最致命的问题,还是在于游戏业务跟字节的核心业务是有直接矛盾的。字节的核心业务是流量,它需要的是用户在信息流中的停留时长,而游戏内容本身就是会去争夺这些使用时长的。
张一鸣对游戏只有功利的期待,作为张一鸣替身的严授能做的,其实就是贯彻这种功利。严当然算不上什么特别出色的领导,但在这么个业务环境下,自己还算干净,居然还有些亮点(比如《Marvel Snap》,比如《晶核》),按照我某个朋友的说法,其实就是一个质疑-理解的过程。
接下来的字节游戏我当然还是不看好,字节保留这些业务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剩下的项目和资产在当前的环境下,无人接盘,HR出身的新掌门人做的,恐怕也只是精简成本和减缓失血。无论如何,这个时代是结束了。
空空如也
暂无小宇宙热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