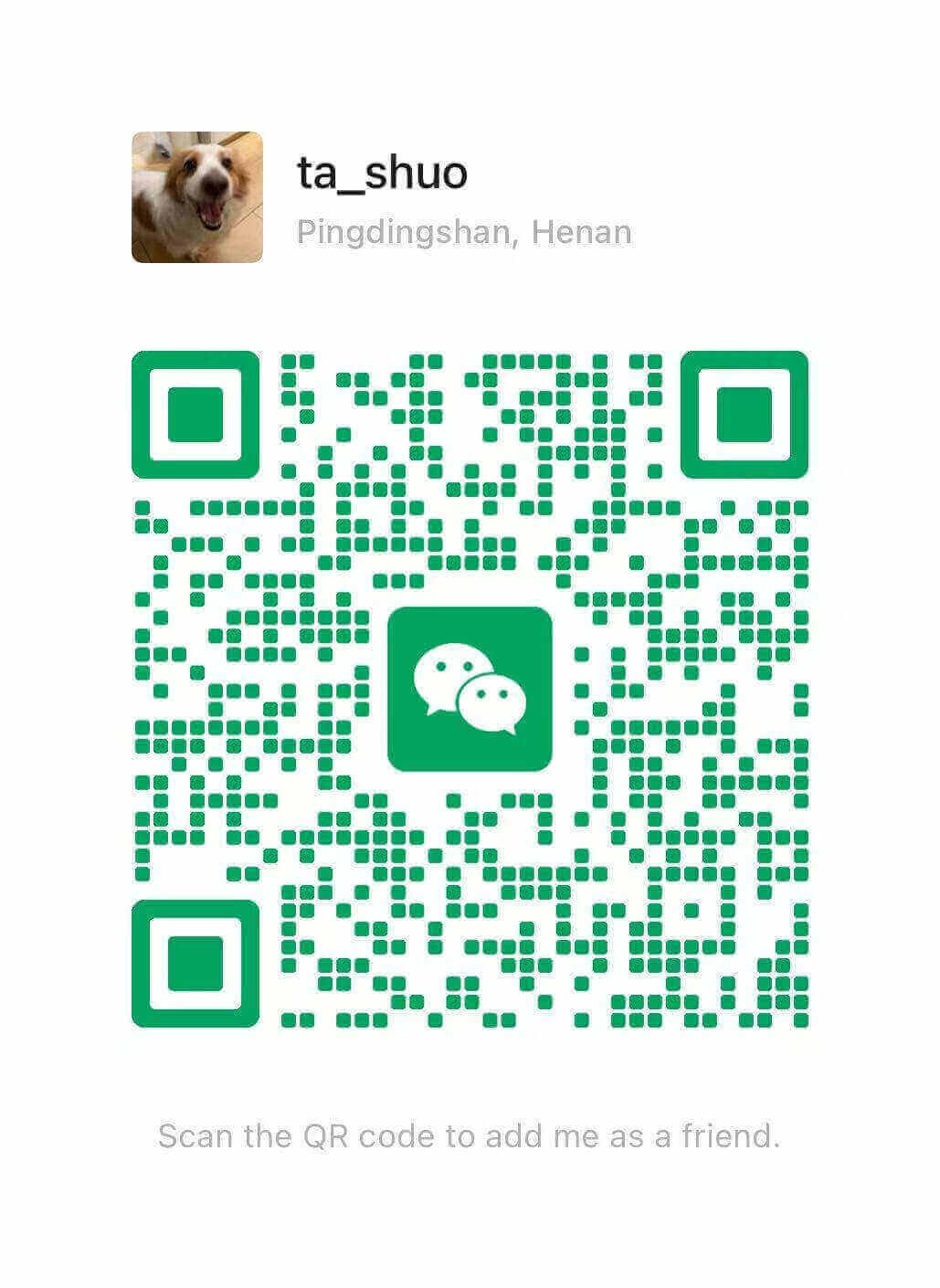时长:
11分钟
播放:
79
发布:
2天前
主播...
简介...
今天是2026年1月11日,一百零六年前的明天,也就是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了一道训令,规定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课本改用白话文教学,并计划逐步废止所有文言文教科书。这道看似普通的行政命令,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中国教育从“精英垄断”走向“大众普及”的大门。今天,我们就从清末民初的课堂讲起,还原这场“白话文入课堂”运动的来龙去脉,看看它如何让文字从古籍中走下来,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要理解这场改革的意义,得先看清当时的教育有多“难”。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可课堂上的课本却还是老样子。孩子们启蒙读《三字经》《千字文》,稍大些学“四书五经”,作文必须用“之乎者也”,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全靠老师断句。1913年,有人在《教育杂志》上记录过一个真实案例:江苏某小学的作文课上,学生写“今日天气晴朗,余与友出游”,老师批注“不通,应作‘今日天朗气清,与友人同游’”,可学生实际想说的是“今天太阳好,我和同学去河边玩”,文言的表达和孩子的生活完全脱节。
更麻烦的是,文言文的学习成本太高。当时全国文盲率超过80%,能读懂《论语》的人不到5%,更别说用文言写作了。1915年,商务印书馆做过一次调查:全国小学毕业生中,能用文言写出通顺书信的不足30%,多数孩子只会背“子曰诗云”,却连一张请假条都写不明白。这种“学非所用”的教育,让知识成了少数人的专利,普通百姓家的孩子,要么在私塾里死记硬背,要么干脆辍学种地。
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为打破这种僵局提供了思想武器。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第一条就是“须言之有物”,他痛批文言“文胜质则史”,说“古人说的‘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现在谁还这么说话?”同一时期,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更激进,喊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这些主张像一声惊雷,让知识界开始反思:教育的目的,难道不是让每个人都能用文字表达自己吗?
钱玄同、刘半农等学者也加入进来。钱玄同说“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直指当时流行的骈文和桐城派古文脱离现实;刘半农则身体力行,用白话翻译外国诗歌,还创办《歌谣》周刊,收集民间俚语,证明“老百姓的话也能登大雅之堂”。这些讨论让“白话文”从一个文学概念,变成了教育改革的焦点。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让白话文从书斋走向街头。学生游行时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白话口号,比文言的“内惩国贼,外争国权”更有力;上海《申报》用白话报道学生火烧赵家楼,比文言的“学子激于义愤,焚曹宅以泄忿”更让百姓看得懂。连最保守的《东方杂志》都开始用白话写评论,主编杜亚泉说:“时代变了,文字也得跟着变,不然怎么跟年轻人说话?”
在这样的氛围下,北洋政府的改革终于迈出了一步。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正式发布训令,原文是“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其余各年级,亦应逐渐改用,务期十年之内,完全废止文言教科书”。这里的“国民学校”就是小学,先让六七岁的孩子用白话学认字,再慢慢过渡到高年级,最后彻底告别文言。
这道训令一发布,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支持者拍手称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说“这是教育界的大革命,从此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玩意儿”;但反对声也不少。山东某县教育局长因坚持用文言教学,被省教育厅撤职,他写信抗议“废文言就是废祖宗之法”;江苏的私塾先生们集体罢课,说“白话文是引车卖浆者之言,岂能登课堂?”还有家长担心“孩子学白话,以后考秀才怎么办?”。
改革的具体实施,比想象中更复杂。首先是教材问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连夜组织学者编写白话文课本。1920年秋季开学,第一套白话文教材送到学校,一年级第一课是“人,手,足,头,身”,配着图画教孩子认字;二年级课文是“妈妈缝衣裳,弟弟画图画,爸爸看报纸,我背书包上学去”,全是生活场景。叶圣陶后来回忆,他编写《开明国语课本》时,特意去小学听课,看孩子们喜欢什么,最后用“萤火虫,提灯笼,飞到西,飞到东”这样的童谣代替道德说教,果然大受欢迎。
但农村地区的推广却困难重重。很多地方没有白话文老师,私塾先生只会教“人之初,性本善”,改教白话文就像让老中医学西医,摸不着头脑。1935年教育部调查河北某县,52所小学里只有3所配了白话文教师,剩下的还是用文言混着白话教,学生作业里常出现“今天天气好,余与友出外游玩”这种半文半白的话。更麻烦的是方言差异,南方孩子学北京官话写的白话文,总觉得“别扭”,老师不得不用当地方言解释,结果“言文一致”变成了“言方一致”,离改革初衷有点远。
不过,改革的成效还是慢慢显现了。1923年,上海《申报》统计,白话文报纸销量是文言报纸的12倍,连卖菜的老太太都能看懂《申报》上的“今日青菜每斤三分”;通俗小说更火,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用白话写市井生活,一年卖了二十万册,比传统章回体小说受欢迎多了。教育方面,1925年全国小学白话文教材使用率从1920年的不足20%涨到70%,学生作文里开始出现“我想当医生,给穷人看病不要钱”这样的直白表达,在文言时代,这种话只能憋在心里。
这场改革还悄悄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过去用文言,讲究“微言大义”,写文章要“藏锋不露”,结果很多人学会了“之乎者也”,却不会独立思考。学了白话文后,孩子们开始问“为什么月亮会圆会缺?”“为什么要交这么多税?”,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正是思想解放的开始。1923年,湖南长沙某小学的作文课上,一个学生写“我讨厌缠足,姐姐的脚裹得像粽子,走路都疼”,老师在评语里写“真情实感,胜过千篇一律的‘二十四孝’故事”,这正是白话文带来的变化——文字不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当然,白话文教育也不是一帆风顺。保守派一直批评“白话文浅薄,丢了传统文化的魂”。1927年,章太炎在苏州演讲时说“文言是中华文化的根,废了文言,就像砍断了树的根”,这话有一定道理——文言文确实承载着两千年的文化典籍,但问题在于,当时的文言文教学已经僵化,成了背诵和考试的工具,而不是理解文化的桥梁。后来的实践证明,白话文并没有“废掉”传统文化,反而让更多人能通过白话译本读懂《史记》《红楼梦》,比如1929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白话版《水浒传》,销量超过百万册,让梁山好汉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
这场改革的深远影响,在今天还能感受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语”和“国文”合并为“语文”,白话文正式成为官方教学语言;我们今天用的课本里,“春天来了,小草绿了”这样的句子,就是从1920年代的白话文教材一步步演变来的。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教育为大众服务”的理念——知识不该藏在古籍里,而该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话讲出来。
回顾1920年1月12日的这道训令,它不只是一次语言改革,更是一场教育民主化的尝试。它让六七岁的孩子不再对着“天地玄黄”发呆,而是能从“狗,大狗,小狗”开始认识世界;让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也能用笔写下自己的想法。尽管过程中有阻力、有妥协,但它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毕竟,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让少数人学会“之乎者也”,而是让每个人都敢用自己的话,说出自己的故事。
当我们今天翻开小学语文课本,看到那些简单的句子时,或许该记住:这背后,是一百年前无数人为“让文字回归生活”所做的努力。
要理解这场改革的意义,得先看清当时的教育有多“难”。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可课堂上的课本却还是老样子。孩子们启蒙读《三字经》《千字文》,稍大些学“四书五经”,作文必须用“之乎者也”,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全靠老师断句。1913年,有人在《教育杂志》上记录过一个真实案例:江苏某小学的作文课上,学生写“今日天气晴朗,余与友出游”,老师批注“不通,应作‘今日天朗气清,与友人同游’”,可学生实际想说的是“今天太阳好,我和同学去河边玩”,文言的表达和孩子的生活完全脱节。
更麻烦的是,文言文的学习成本太高。当时全国文盲率超过80%,能读懂《论语》的人不到5%,更别说用文言写作了。1915年,商务印书馆做过一次调查:全国小学毕业生中,能用文言写出通顺书信的不足30%,多数孩子只会背“子曰诗云”,却连一张请假条都写不明白。这种“学非所用”的教育,让知识成了少数人的专利,普通百姓家的孩子,要么在私塾里死记硬背,要么干脆辍学种地。
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为打破这种僵局提供了思想武器。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第一条就是“须言之有物”,他痛批文言“文胜质则史”,说“古人说的‘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现在谁还这么说话?”同一时期,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更激进,喊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这些主张像一声惊雷,让知识界开始反思:教育的目的,难道不是让每个人都能用文字表达自己吗?
钱玄同、刘半农等学者也加入进来。钱玄同说“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直指当时流行的骈文和桐城派古文脱离现实;刘半农则身体力行,用白话翻译外国诗歌,还创办《歌谣》周刊,收集民间俚语,证明“老百姓的话也能登大雅之堂”。这些讨论让“白话文”从一个文学概念,变成了教育改革的焦点。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让白话文从书斋走向街头。学生游行时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白话口号,比文言的“内惩国贼,外争国权”更有力;上海《申报》用白话报道学生火烧赵家楼,比文言的“学子激于义愤,焚曹宅以泄忿”更让百姓看得懂。连最保守的《东方杂志》都开始用白话写评论,主编杜亚泉说:“时代变了,文字也得跟着变,不然怎么跟年轻人说话?”
在这样的氛围下,北洋政府的改革终于迈出了一步。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正式发布训令,原文是“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其余各年级,亦应逐渐改用,务期十年之内,完全废止文言教科书”。这里的“国民学校”就是小学,先让六七岁的孩子用白话学认字,再慢慢过渡到高年级,最后彻底告别文言。
这道训令一发布,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支持者拍手称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说“这是教育界的大革命,从此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玩意儿”;但反对声也不少。山东某县教育局长因坚持用文言教学,被省教育厅撤职,他写信抗议“废文言就是废祖宗之法”;江苏的私塾先生们集体罢课,说“白话文是引车卖浆者之言,岂能登课堂?”还有家长担心“孩子学白话,以后考秀才怎么办?”。
改革的具体实施,比想象中更复杂。首先是教材问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连夜组织学者编写白话文课本。1920年秋季开学,第一套白话文教材送到学校,一年级第一课是“人,手,足,头,身”,配着图画教孩子认字;二年级课文是“妈妈缝衣裳,弟弟画图画,爸爸看报纸,我背书包上学去”,全是生活场景。叶圣陶后来回忆,他编写《开明国语课本》时,特意去小学听课,看孩子们喜欢什么,最后用“萤火虫,提灯笼,飞到西,飞到东”这样的童谣代替道德说教,果然大受欢迎。
但农村地区的推广却困难重重。很多地方没有白话文老师,私塾先生只会教“人之初,性本善”,改教白话文就像让老中医学西医,摸不着头脑。1935年教育部调查河北某县,52所小学里只有3所配了白话文教师,剩下的还是用文言混着白话教,学生作业里常出现“今天天气好,余与友出外游玩”这种半文半白的话。更麻烦的是方言差异,南方孩子学北京官话写的白话文,总觉得“别扭”,老师不得不用当地方言解释,结果“言文一致”变成了“言方一致”,离改革初衷有点远。
不过,改革的成效还是慢慢显现了。1923年,上海《申报》统计,白话文报纸销量是文言报纸的12倍,连卖菜的老太太都能看懂《申报》上的“今日青菜每斤三分”;通俗小说更火,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用白话写市井生活,一年卖了二十万册,比传统章回体小说受欢迎多了。教育方面,1925年全国小学白话文教材使用率从1920年的不足20%涨到70%,学生作文里开始出现“我想当医生,给穷人看病不要钱”这样的直白表达,在文言时代,这种话只能憋在心里。
这场改革还悄悄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过去用文言,讲究“微言大义”,写文章要“藏锋不露”,结果很多人学会了“之乎者也”,却不会独立思考。学了白话文后,孩子们开始问“为什么月亮会圆会缺?”“为什么要交这么多税?”,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正是思想解放的开始。1923年,湖南长沙某小学的作文课上,一个学生写“我讨厌缠足,姐姐的脚裹得像粽子,走路都疼”,老师在评语里写“真情实感,胜过千篇一律的‘二十四孝’故事”,这正是白话文带来的变化——文字不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当然,白话文教育也不是一帆风顺。保守派一直批评“白话文浅薄,丢了传统文化的魂”。1927年,章太炎在苏州演讲时说“文言是中华文化的根,废了文言,就像砍断了树的根”,这话有一定道理——文言文确实承载着两千年的文化典籍,但问题在于,当时的文言文教学已经僵化,成了背诵和考试的工具,而不是理解文化的桥梁。后来的实践证明,白话文并没有“废掉”传统文化,反而让更多人能通过白话译本读懂《史记》《红楼梦》,比如1929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白话版《水浒传》,销量超过百万册,让梁山好汉的故事走进了千家万户。
这场改革的深远影响,在今天还能感受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语”和“国文”合并为“语文”,白话文正式成为官方教学语言;我们今天用的课本里,“春天来了,小草绿了”这样的句子,就是从1920年代的白话文教材一步步演变来的。更重要的是,它确立了“教育为大众服务”的理念——知识不该藏在古籍里,而该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话讲出来。
回顾1920年1月12日的这道训令,它不只是一次语言改革,更是一场教育民主化的尝试。它让六七岁的孩子不再对着“天地玄黄”发呆,而是能从“狗,大狗,小狗”开始认识世界;让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也能用笔写下自己的想法。尽管过程中有阻力、有妥协,但它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毕竟,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让少数人学会“之乎者也”,而是让每个人都敢用自己的话,说出自己的故事。
当我们今天翻开小学语文课本,看到那些简单的句子时,或许该记住:这背后,是一百年前无数人为“让文字回归生活”所做的努力。
评价...
空空如也
小宇宙热门评论...
暂无小宇宙热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