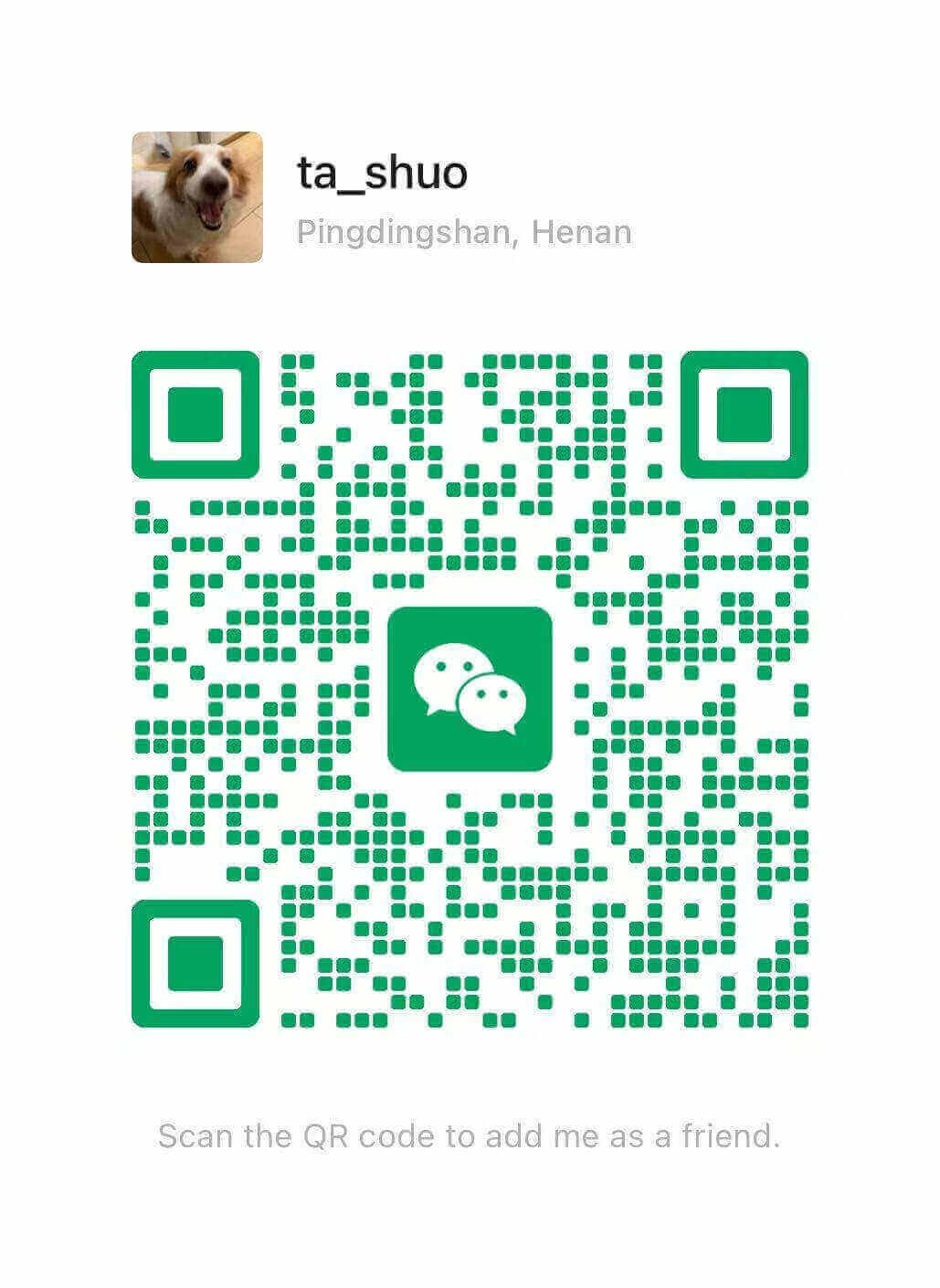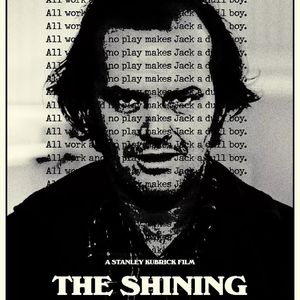
时长:
6分钟
播放:
11
发布:
15小时前
简介...
你有没有想过,一部四十多年前的恐怖片,为什么今天看起来反而更让人脊背发凉?不是因为特效多吓人,也不是因为鬼魂多狰狞,而是因为——它说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闪灵》。这个名字你可能熟,但它的深意,很多人其实没真正看懂。
库布里克是谁?1928年出生在纽约,最早是个杂志摄影师,后来拿起了摄影机,成了好莱坞体系里最“不合群”的导演。他不讨好观众,不妥协制片厂,甚至被叫作“片场暴君”。但他拍出来的电影,像《2001:太空漫游》,是仰望星空的哲学诗;而《闪灵》,则是扎进现实泥潭的一把刀——锋利、冰冷,直指人心。
现在,《闪灵》的4K修复版终于在内地大银幕上映了。但比画质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那近乎预言般的力量。当你再次走进那座被大雪封山的远望酒店,你会发现,库布里克讲的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鬼屋故事。他用这座酒店,映照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困境:历史被遗忘、劳动失去意义、真实被幻象取代,而我们,是不是也正被困在各自的“远望酒店”里?
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从诞生起就是一场“背叛”。原著作者斯蒂芬·金很不满,觉得库布里克“想得太多,感受太少”,把主角杰克复杂的内心挣扎简化成了一条直线的堕落。但恰恰是这种“简化”,暴露了库布里克真正的意图——他根本不想拍一个家庭崩溃的超自然故事,他要的是寓言,是隐喻,是一场用影像写就的社会诊断书。
你看那些细节:原著里的217号房间,被他改成237号——这个数字暗合登月阴谋论;酒店的走廊永远走不出去,布局违背欧几里得几何;地毯上全是印第安箭头图案;小丹尼穿的毛衣,印着阿波罗11号。这些都不是随便选的。库布里克把每一个道具、每一帧画面,都变成了密码。他甚至用交叉叠映、时间跳切这些纯电影语言,把一个改编剧本,硬生生升维成一场多声部的思想实验。
当然,这种极致追求是有代价的。传说中,为了让谢莉·杜瓦尔演出那种真实的惊恐,一场棒球棍戏拍了127次。她后来精神崩溃,几乎无法继续工作。我们很难说这种创作方式对不对,但不可否认,正是这种近乎残酷的控制,才让影片里那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如此真实——库布里克要的从来不是Jump Scare(突然惊吓),而是把恐怖种进你的潜意识,等你多年后某天突然意识到:原来那场噩梦,一直都在。
那么问题来了:远望酒店到底是什么?它真的是闹鬼吗?不,它是一个庞大的隐喻系统。首先,它是美国殖民暴力的历史坟场。酒店建在印第安人的墓地上,墙上的纹饰、地毯的图案,都是无声的控诉。杰克挥舞斧头劈门的那一幕,和西进运动中对原住民的屠杀,形成了可怕的镜像。更瘆人的是,前任看守格雷迪对他说:“你一直是酒店的看守。”这句话什么意思?意思是,暴力不是偶然的,它有传承,有宿主,而杰克,只是最新一代的容器。
再往深了看,这座酒店还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完美象征。杰克那台打字机上,反复只有一句话:“只工作不玩耍,聪明杰克也变傻。”这哪是写作瓶颈?这分明是当代人的真实写照——我们日复一日做着重复劳动,创造力枯竭,想象力死亡。酒店金色大厅里播放的怀旧音乐,营造的不是温情,而是一种“被净化过的历史幻象”,让我们沉溺在过去,逃避当下的空洞。而那场电梯涌出滔天血潮的镜头,今天看来,简直是对金融资本无序扩张最骇人的视觉隐喻。
库布里克在1980年就预见到:未来的世界,会被信息茧房包裹,历史感会越来越薄,真实会被精心包装的幻象取代。而我们每个人,某种程度上,不都是杰克吗?被困在自己的精神牢笼里,被看不见的力量驱使,重复着无意义的动作,一步步走向疯狂。
但库布里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这些沉重的批判,全都藏在了极致的视听体验里。那永远走不出去的迷宫,既是殖民暴力的循环,也是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外化。他用日历卡片的快速跳切,表现时间的空洞流逝——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复制,对应着那句“没有别的选择”的资本主义咒语。就连声音都被赋予了批判功能: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在大厅响起,非但不显高雅,反而暴露了所谓“文明”的虚伪;电视的噪音,则是历史真相被干扰、被掩盖的嘶嘶声。
可就在这一切令人窒息的黑暗深处,库布里克真的没留一点光吗?有。这光,就在丹尼身上。影片最后那场迷宫追逐,丹尼做了一件他父亲永远做不到的事:他倒退着走,在雪地上留下错误的脚印。这不是小聪明,这是对历史循环的破解——他用空间策略,打破了时间的诅咒。而杰克呢?冻死在迷宫中心,身体姿势竟和地毯上的印第安箭头完全一致。施暴者最终被自己信奉的暴力图腾反噬,这是一个宿命的闭环。
但丹尼和母亲温蒂开车离开了。这个离开很虚弱,甚至狼狈,但它是一个姿态——新一代,或许真有打破循环的可能。温蒂手里那根笨拙挥舞的棒球棍,曾被嘲讽为“无产阶级反抗的拙劣模仿”,但正是这种源自生存本能的、不完美的反抗,救了他们。
所以,《闪灵》的伟大,正在于它的复杂。它既是一面照见历史伤疤的魔镜,也是一则关于当下异化的精准预言,同时,它也没有彻底熄灭希望的火星。四十六年过去,当年被说“过度解读”的文本,如今却越来越清晰地应验在我们身上。当你在信息洪流中迷失,在重复劳动中感到虚无,在怀旧滤镜里逃避现实时,远望酒店那条悠长、对称、看似通向光明实则永无出口的走廊,或许早已在你心里悄然延伸。
库布里克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或者是否有能力,像丹尼一样,识破迷宫的诡计,找到那条走出去的小径?他的电影从不给轻易的答案,他只负责呈现冰山一角,而水面之下那庞大而黑暗的部分,需要每个时代的观众,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去丈量、去思考。这,或许就是“作者电影”所能抵达的最深远的意义。
库布里克是谁?1928年出生在纽约,最早是个杂志摄影师,后来拿起了摄影机,成了好莱坞体系里最“不合群”的导演。他不讨好观众,不妥协制片厂,甚至被叫作“片场暴君”。但他拍出来的电影,像《2001:太空漫游》,是仰望星空的哲学诗;而《闪灵》,则是扎进现实泥潭的一把刀——锋利、冰冷,直指人心。
现在,《闪灵》的4K修复版终于在内地大银幕上映了。但比画质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那近乎预言般的力量。当你再次走进那座被大雪封山的远望酒店,你会发现,库布里克讲的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鬼屋故事。他用这座酒店,映照出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困境:历史被遗忘、劳动失去意义、真实被幻象取代,而我们,是不是也正被困在各自的“远望酒店”里?
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从诞生起就是一场“背叛”。原著作者斯蒂芬·金很不满,觉得库布里克“想得太多,感受太少”,把主角杰克复杂的内心挣扎简化成了一条直线的堕落。但恰恰是这种“简化”,暴露了库布里克真正的意图——他根本不想拍一个家庭崩溃的超自然故事,他要的是寓言,是隐喻,是一场用影像写就的社会诊断书。
你看那些细节:原著里的217号房间,被他改成237号——这个数字暗合登月阴谋论;酒店的走廊永远走不出去,布局违背欧几里得几何;地毯上全是印第安箭头图案;小丹尼穿的毛衣,印着阿波罗11号。这些都不是随便选的。库布里克把每一个道具、每一帧画面,都变成了密码。他甚至用交叉叠映、时间跳切这些纯电影语言,把一个改编剧本,硬生生升维成一场多声部的思想实验。
当然,这种极致追求是有代价的。传说中,为了让谢莉·杜瓦尔演出那种真实的惊恐,一场棒球棍戏拍了127次。她后来精神崩溃,几乎无法继续工作。我们很难说这种创作方式对不对,但不可否认,正是这种近乎残酷的控制,才让影片里那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如此真实——库布里克要的从来不是Jump Scare(突然惊吓),而是把恐怖种进你的潜意识,等你多年后某天突然意识到:原来那场噩梦,一直都在。
那么问题来了:远望酒店到底是什么?它真的是闹鬼吗?不,它是一个庞大的隐喻系统。首先,它是美国殖民暴力的历史坟场。酒店建在印第安人的墓地上,墙上的纹饰、地毯的图案,都是无声的控诉。杰克挥舞斧头劈门的那一幕,和西进运动中对原住民的屠杀,形成了可怕的镜像。更瘆人的是,前任看守格雷迪对他说:“你一直是酒店的看守。”这句话什么意思?意思是,暴力不是偶然的,它有传承,有宿主,而杰克,只是最新一代的容器。
再往深了看,这座酒店还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完美象征。杰克那台打字机上,反复只有一句话:“只工作不玩耍,聪明杰克也变傻。”这哪是写作瓶颈?这分明是当代人的真实写照——我们日复一日做着重复劳动,创造力枯竭,想象力死亡。酒店金色大厅里播放的怀旧音乐,营造的不是温情,而是一种“被净化过的历史幻象”,让我们沉溺在过去,逃避当下的空洞。而那场电梯涌出滔天血潮的镜头,今天看来,简直是对金融资本无序扩张最骇人的视觉隐喻。
库布里克在1980年就预见到:未来的世界,会被信息茧房包裹,历史感会越来越薄,真实会被精心包装的幻象取代。而我们每个人,某种程度上,不都是杰克吗?被困在自己的精神牢笼里,被看不见的力量驱使,重复着无意义的动作,一步步走向疯狂。
但库布里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这些沉重的批判,全都藏在了极致的视听体验里。那永远走不出去的迷宫,既是殖民暴力的循环,也是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外化。他用日历卡片的快速跳切,表现时间的空洞流逝——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复制,对应着那句“没有别的选择”的资本主义咒语。就连声音都被赋予了批判功能: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在大厅响起,非但不显高雅,反而暴露了所谓“文明”的虚伪;电视的噪音,则是历史真相被干扰、被掩盖的嘶嘶声。
可就在这一切令人窒息的黑暗深处,库布里克真的没留一点光吗?有。这光,就在丹尼身上。影片最后那场迷宫追逐,丹尼做了一件他父亲永远做不到的事:他倒退着走,在雪地上留下错误的脚印。这不是小聪明,这是对历史循环的破解——他用空间策略,打破了时间的诅咒。而杰克呢?冻死在迷宫中心,身体姿势竟和地毯上的印第安箭头完全一致。施暴者最终被自己信奉的暴力图腾反噬,这是一个宿命的闭环。
但丹尼和母亲温蒂开车离开了。这个离开很虚弱,甚至狼狈,但它是一个姿态——新一代,或许真有打破循环的可能。温蒂手里那根笨拙挥舞的棒球棍,曾被嘲讽为“无产阶级反抗的拙劣模仿”,但正是这种源自生存本能的、不完美的反抗,救了他们。
所以,《闪灵》的伟大,正在于它的复杂。它既是一面照见历史伤疤的魔镜,也是一则关于当下异化的精准预言,同时,它也没有彻底熄灭希望的火星。四十六年过去,当年被说“过度解读”的文本,如今却越来越清晰地应验在我们身上。当你在信息洪流中迷失,在重复劳动中感到虚无,在怀旧滤镜里逃避现实时,远望酒店那条悠长、对称、看似通向光明实则永无出口的走廊,或许早已在你心里悄然延伸。
库布里克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或者是否有能力,像丹尼一样,识破迷宫的诡计,找到那条走出去的小径?他的电影从不给轻易的答案,他只负责呈现冰山一角,而水面之下那庞大而黑暗的部分,需要每个时代的观众,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去丈量、去思考。这,或许就是“作者电影”所能抵达的最深远的意义。
评价...
空空如也
小宇宙热门评论...
暂无小宇宙热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