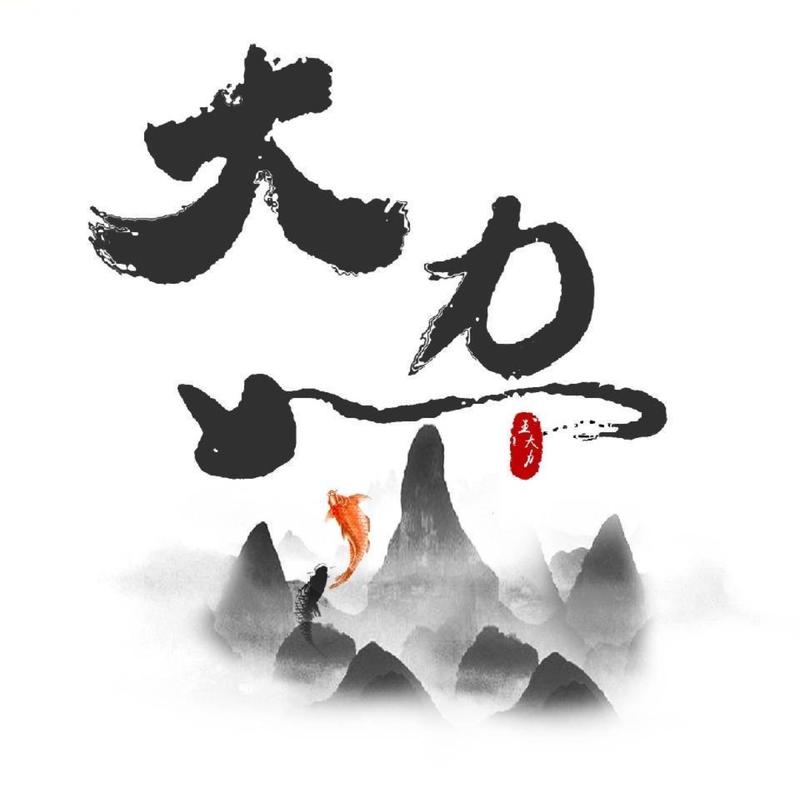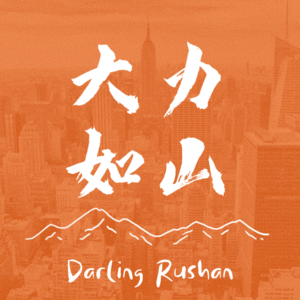
时长:
76分钟
播放:
1,402
发布:
3个月前
主播...
简介...
这是一档关注金融从业者和已退休从业者的栏目,主理人是王大力。
大家好久不见。没错,因为我这段时间跑去了成都又参加公益领域的培训去了,混沌创益院第九期:
从9月开始去学,到现在已经学俩月了,每个月要连学三天,每天都是白天从早九点上课上到晚九点,然后回酒店后还得继续熬夜写作业,我只能说学习真得是太苦了,而且到现在我都没学完,下个月还要接着去成都再学三天。
好在这三个月培训的地方都是在成都,一个培训地点随便在哪周围都可以找到还不错馆子的地方。当然,我并不是为了吃才去参加培训的,而是为了拿锦旗才去的:
哈哈哈,开个玩笑,我当然是为了学习才去的,毕竟这个培训不仅要真金白银交学费,而且还得通过创益院的沈杰院长亲自面试通过才能参加的。所以我确实是很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毕竟作为公益新人,在这个跟公益相关的培训班里,遇到的老师包括同学可以说全都是我在公益领域的“前辈”。
比如今天这期播客的嘉宾强子(李强 益微青年总干事),不仅是我的九期班同学,还是我所在小组的同学,而他虽然是比我年轻的90后,却还是大学一毕业就加入益微做了十几年青年公益的“前辈”。
我一认识强子后就挺羡慕他的,20多岁的时候就走上了我快40岁才走上的道路,跟他相比我总觉得是自己多走了20年弯路,所以真的特别好奇他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啥家庭啥背景啊?
所以当强子在这期播客里跟我分享他在大学读理工科时的迷茫,是如何在大学创建公益社团,然后遇到了自己在公益路上的“导师”觉醒,又看着益微青年的出生,一路陪着走到了现在。我听完后更羡慕他20岁就觉醒的生命状态了,毕竟我在金融行业卷到30多岁提前退休后才尝到了公益的滋养。
而那天为了录播客,当我第一次走进他们在成都的“艰苦”办公室时,就更好奇这个在青年公益领域扎根了二十多年,如今每年要办100场活动,招募1000名大学生志愿者,累计支持了几万名大学生服务了十几万乡村儿童的头部公益组织:EV,竟然在这么一个房租便宜到我猜都猜不出来的居民楼里办公?所以做公益就一定会这么苦?就非得那么苦?
直到听强子在播客里分享了益微这么些年的发展历程,我才知道这条他们已经走了二十多年的路,不仅仅是办公条件苦,还踩过资金断裂、志愿者断层的坑,好在也攒下不少被服务者又回来当志愿者的暖。
我也是才知道,听起来很传统的大学生支教活动,早在十年前就被他们升级为了2.0,从原来大学生去村里过两周“送知识”,更新为一场把城市青年和乡村孩子聚在一起,从“我来教你”变成“我们一起玩”,把1.0的“短期支教”升级成了2.0的“乡村夏令营”。
扎心的是他们做了十多年的2.0,最近几年发现如今大学生群体又变了,开始从“我什么都能干”变成了“你得把我安排好”,如今的他们又要开始一轮新的3.0需求迭代......
虽然这期播客不是为了煽情,但确实也说了很多公益的苦,比如项目制的困局、月捐的天花板、苦行僧式的成本观等等......如果你也好奇“青年”这个看似非弱势的群体,为什么仍值得被关注被投资,为什么益微这样的公益组织仍继续关注和投资,那就戴上耳机,跟我们一起把这个公益领域里的“冷门”听个明白吧:
-时间轴-
02:21 怎么青年公益组织感觉都是“益”家人?
“为什么青年组织的名称都选用‘益’字呢?益微青年的‘益’其实是音译过来的,我们的英文叫enjoy volunteering,取首字母大写就是E和V,乐享志愿的意思。当然也有它的字面表述:公益,微小改变。”
“大三那年,我看到安东尼·罗宾在上海的一场演讲。他提及成功的五个法则,最后一个法则是做慈善。其他几个法则我都不具备,只有做慈善力所能及。我就在学校里做了一个公益社团,因为看不惯当时我们理工类学校的某些风气,似乎去运动会捡个垃圾就叫作奉献了。去敬老院或者福利院,恨不得一个脚三个人洗。我觉得好无趣。”
“在益微青年领导力工作坊,我见到了人生导师、领路人之一柚子。我觉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命状态——不是通过竞争来干掉你,而是打心底去欣赏你和成就你。”
09:36 因为公益不是通过竞争来干掉别人,而是打心底欣赏和成就你
“大二我们有一门课叫微机原理。老师第一次上台就跟我们说,这门课是20年前的课,未来也用不上,但是你们得学。这句话一下就击碎我了。一个大学正在教的就是那些20年前有用、但未来一定用不了的东西。而且老师也自知。那我还学来干嘛?”
“我的生存策略就是想要自己蹚出一条路。这条路径不适合我,我也卷不动,当下我对成功没有那么大的偏执了。而在公益领域里我看到一个更完整的自己,比如说我第一次当众哭……”
“在学校里没人看中这些东西。但在那个时候有人在意,你就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被看见了,这就会极大地滋养到我。而且他不光是看见我,还给我很真实的反馈。他觉得我可以更真实一点。你很难想象我以前像个机器一样,对什么都客客气气,很正经。”
15:09 公益组织生存实录,出差都要拼房睡?
“有一个让我特别震撼的事实:每次参加培训之前会拉班级群,我总发现群里有人要拼房。关键是如果我们去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房价比较贵,拼房我也可以理解。但像咱们第一阶段酒店,一晚上二百多块钱,在一线城市是很便宜的价格。这就证明这些人并不是为了省钱,而是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能省则省。他不是说住不起,因为我看到了五百多、六百多的酒店有人拼,二百多的还有人拼。在我熟悉的金融领域,反正没见过这种事。”
“这就涉及公益组织的一个困境。困境有两层:一个是项目制的困境,另外一个是行业监管困境。公益组织的资金都是按项目以年为期结算的,你不知道第二年项目资方是否会继续花钱。所以在成本上我们会刻意地分配,不在非必要的地方投入太多。”
“行业也在收缩。原来月捐是组织的非限定经费,我们可以跟月捐人沟通如何分配使用。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分配在人力上的成本不能超过多少比例。我们得把月捐这么珍贵的钱花出去,一部分给到实际项目里的支出,只留大概20%~30%覆盖人力成本。筹款上感觉被扼住了脖子。”
22:27 益微的两个十年进化:从大学生支教1.0到乡村夏令营2.0
“1998到2002年,西北师范大学的学生骑行中国,拍了很多中国西部农村的真实图片。之后他在北京做了场高校图片展,一下子点燃了主流高校的热情。那时候大家会有一种宏大叙事感,认为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乡村,还有没有桌椅的学校?我作为一个天之骄子,想去贡献一份力量。”
“在那场营会上,我见证了益微青年的诞生。冥冥之中有种命运的齿轮被拨动的感觉,我看到孩子呱呱坠地,就想陪孩子多走几步,所以一直陪伴益微青年到现在。”
“参加乡村夏令营后,你的底层信念会发生变化。乡村夏令营不太强调知识改变命运,也不鼓励你非得跟孩子说,要考上大学,跟我见面,才算是成功的人生。不是。乡村夏令营更多会去做一些关于乡土、运动、社会情感的事情,关于底层能力的发展,学习兴趣的激发。它重新塑造了教和学的关系,在这里我们都是平等的。”
34:16 “长大后我就成了谁?”
“Ta到大学后,那个藏宝袋一直没丢,里面珍藏着哥哥姐姐,还有同学给ta写的话。特别巧,藏宝袋的信封上印了益微青年的信息。某天ta拿出来翻看,上网搜了一下益微青年,刚好看到公众号在招募志愿者,最后报名通过,就继续参与活动了,而且服务的对象正是ta以前学校里的孩子。”
“严峻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会把你作为服务提供者,评判你的服务到不到位。我做支教,投入时间和精力,但是你好像没有给我提供特别好的教学环境。我只是来上课,但是你们还让我自己做饭,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简直不能理解。”
“这种张力会越来越大。做完洞察后,我们发现其实不只是大学,从小学教育开始,他的竞争倾向或者说目标聚焦就一直存在。我要不择手段达成目的,获得这样的机会,把别人挤下去。所以他会有更功利的诉求。”
42:59 公益传播的困境:组织都很好,但我们不知道
“刚才介绍了这么多组织,做的项目都这么厉害,我有种感受是为啥才知道呢?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处的学校、城市都很前沿,这么些年仍然不太了解。这是我的问题,他们的问题,还是社会组织的问题呢?”
“分享一组数据:大学生参与公益,60%的原因是在线下接触过相关信息。比如宣讲会或者是同学介绍,这是转化率最高的渠道。反倒线上可能就是10%~20%的转化率。”
“报名公益之前,大家非常在意的一点就是安全和靠谱。你这组织会不会把我送到一个地方,乱收钱,甚至让我身陷危机。对于没听说过的组织一视同仁,我都要了解一下你算不算靠谱。靠谱的定义就是有没有国家、政府、高校的背书。他们现在信息更多,选择反倒更窄了。”
52:40 受助群体“鄙视链”:老人、小孩、妇女优先,而青年排在动物之后?
“之前我们做行业扫描,当时有乡村夏令营项目的组织大概有七十多家。现在再做扫描就只剩三四十家了,近乎腰斩。因为这是一个重线下的项目,人力投入比较多,但是吃力不讨好。由于资金链断裂,或者创始人有其他的发展,就流失掉一部分。”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受助对象的选择就会有所倾斜。比如在城市和乡村肯定选乡村。乡村里的老人、小孩,妇女,接着是动物,青年排在动物之后。而金融青年还要排在青年之后。”
“现在的大学生我们定义为生命力受损。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所有的教育压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然后大学高中化,又面临这么大的就业压力,承担这么多的社会期待以及自我生存的期待。甚至现在大家会觉得啃老就是最省钱的办法。”
01:02:05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青年“非优势群体”?
“有些人会认为既然我做了公益,你就应该帮我。你不帮我就是你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如果有这种思想和意识,别人会有被道德绑架之感,为什么要帮你?”
“最终我看到很多青年社会组织,有的变成了社会企业,甚至变成商业机构,比如广州的xxxx。你们益微青年有想过朝那个方向或者领域去发展、变革吗?”
“公益要激发参与,然后建立信任。我们设计机制,让第三方愿意为这件事情买单,参与进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让大家看到我参与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承担这个成本,但是有什么样的资金流主动帮我承担了成本。而在过程当中我贡献了什么,以及收获了什么。这会是一个更加健康的参与状态。”
01:08:59 公益组织的共识:孤独、无力与希望
“今年痛定思痛了,我们得在当下做出一个清醒的认知,就是怎么让这件事情更可持续下去。现在无论是筹款量还是参与率都在逐年下滑,我们真的危机感很强。”
“在既有手段上要做一些怎样的迭代,可能是更轻量级,或者是更能满足功能性需求的调整。我们确实更强调情感性的联结,比如社交、成长、领导力提升。”
“梁晓燕老师是中国公益领域教母级别的角色,她同时做环保和教育领域。她有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做环保会更有无力感,因为你没办法单一解决整体环境问题。但是做教育反倒是很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个体。你不一定影响了100、1000万人,但是你对一个人的生命,会有这样的点燃或影响。”
-关于大力如山-
券业最野自媒体、原券商投行业务条线董事总经理、畅销书《投行职业进阶指南:从新手到合伙人》作者。创建了公益组织:金融职业发展专项基金
【每周直播预约及回看】
视频号:大力如山
【互动平台】
微信公众号:大力如山
微博@王大力如山
小红书:大力如山
【书籍】《投行职业进阶指南》(各大购书网站均有售)
大家好久不见。没错,因为我这段时间跑去了成都又参加公益领域的培训去了,混沌创益院第九期:
从9月开始去学,到现在已经学俩月了,每个月要连学三天,每天都是白天从早九点上课上到晚九点,然后回酒店后还得继续熬夜写作业,我只能说学习真得是太苦了,而且到现在我都没学完,下个月还要接着去成都再学三天。
好在这三个月培训的地方都是在成都,一个培训地点随便在哪周围都可以找到还不错馆子的地方。当然,我并不是为了吃才去参加培训的,而是为了拿锦旗才去的:
哈哈哈,开个玩笑,我当然是为了学习才去的,毕竟这个培训不仅要真金白银交学费,而且还得通过创益院的沈杰院长亲自面试通过才能参加的。所以我确实是很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毕竟作为公益新人,在这个跟公益相关的培训班里,遇到的老师包括同学可以说全都是我在公益领域的“前辈”。
比如今天这期播客的嘉宾强子(李强 益微青年总干事),不仅是我的九期班同学,还是我所在小组的同学,而他虽然是比我年轻的90后,却还是大学一毕业就加入益微做了十几年青年公益的“前辈”。
我一认识强子后就挺羡慕他的,20多岁的时候就走上了我快40岁才走上的道路,跟他相比我总觉得是自己多走了20年弯路,所以真的特别好奇他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啥家庭啥背景啊?
所以当强子在这期播客里跟我分享他在大学读理工科时的迷茫,是如何在大学创建公益社团,然后遇到了自己在公益路上的“导师”觉醒,又看着益微青年的出生,一路陪着走到了现在。我听完后更羡慕他20岁就觉醒的生命状态了,毕竟我在金融行业卷到30多岁提前退休后才尝到了公益的滋养。
而那天为了录播客,当我第一次走进他们在成都的“艰苦”办公室时,就更好奇这个在青年公益领域扎根了二十多年,如今每年要办100场活动,招募1000名大学生志愿者,累计支持了几万名大学生服务了十几万乡村儿童的头部公益组织:EV,竟然在这么一个房租便宜到我猜都猜不出来的居民楼里办公?所以做公益就一定会这么苦?就非得那么苦?
直到听强子在播客里分享了益微这么些年的发展历程,我才知道这条他们已经走了二十多年的路,不仅仅是办公条件苦,还踩过资金断裂、志愿者断层的坑,好在也攒下不少被服务者又回来当志愿者的暖。
我也是才知道,听起来很传统的大学生支教活动,早在十年前就被他们升级为了2.0,从原来大学生去村里过两周“送知识”,更新为一场把城市青年和乡村孩子聚在一起,从“我来教你”变成“我们一起玩”,把1.0的“短期支教”升级成了2.0的“乡村夏令营”。
扎心的是他们做了十多年的2.0,最近几年发现如今大学生群体又变了,开始从“我什么都能干”变成了“你得把我安排好”,如今的他们又要开始一轮新的3.0需求迭代......
虽然这期播客不是为了煽情,但确实也说了很多公益的苦,比如项目制的困局、月捐的天花板、苦行僧式的成本观等等......如果你也好奇“青年”这个看似非弱势的群体,为什么仍值得被关注被投资,为什么益微这样的公益组织仍继续关注和投资,那就戴上耳机,跟我们一起把这个公益领域里的“冷门”听个明白吧:
-时间轴-
02:21 怎么青年公益组织感觉都是“益”家人?
“为什么青年组织的名称都选用‘益’字呢?益微青年的‘益’其实是音译过来的,我们的英文叫enjoy volunteering,取首字母大写就是E和V,乐享志愿的意思。当然也有它的字面表述:公益,微小改变。”
“大三那年,我看到安东尼·罗宾在上海的一场演讲。他提及成功的五个法则,最后一个法则是做慈善。其他几个法则我都不具备,只有做慈善力所能及。我就在学校里做了一个公益社团,因为看不惯当时我们理工类学校的某些风气,似乎去运动会捡个垃圾就叫作奉献了。去敬老院或者福利院,恨不得一个脚三个人洗。我觉得好无趣。”
“在益微青年领导力工作坊,我见到了人生导师、领路人之一柚子。我觉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命状态——不是通过竞争来干掉你,而是打心底去欣赏你和成就你。”
09:36 因为公益不是通过竞争来干掉别人,而是打心底欣赏和成就你
“大二我们有一门课叫微机原理。老师第一次上台就跟我们说,这门课是20年前的课,未来也用不上,但是你们得学。这句话一下就击碎我了。一个大学正在教的就是那些20年前有用、但未来一定用不了的东西。而且老师也自知。那我还学来干嘛?”
“我的生存策略就是想要自己蹚出一条路。这条路径不适合我,我也卷不动,当下我对成功没有那么大的偏执了。而在公益领域里我看到一个更完整的自己,比如说我第一次当众哭……”
“在学校里没人看中这些东西。但在那个时候有人在意,你就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被看见了,这就会极大地滋养到我。而且他不光是看见我,还给我很真实的反馈。他觉得我可以更真实一点。你很难想象我以前像个机器一样,对什么都客客气气,很正经。”
15:09 公益组织生存实录,出差都要拼房睡?
“有一个让我特别震撼的事实:每次参加培训之前会拉班级群,我总发现群里有人要拼房。关键是如果我们去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房价比较贵,拼房我也可以理解。但像咱们第一阶段酒店,一晚上二百多块钱,在一线城市是很便宜的价格。这就证明这些人并不是为了省钱,而是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能省则省。他不是说住不起,因为我看到了五百多、六百多的酒店有人拼,二百多的还有人拼。在我熟悉的金融领域,反正没见过这种事。”
“这就涉及公益组织的一个困境。困境有两层:一个是项目制的困境,另外一个是行业监管困境。公益组织的资金都是按项目以年为期结算的,你不知道第二年项目资方是否会继续花钱。所以在成本上我们会刻意地分配,不在非必要的地方投入太多。”
“行业也在收缩。原来月捐是组织的非限定经费,我们可以跟月捐人沟通如何分配使用。但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分配在人力上的成本不能超过多少比例。我们得把月捐这么珍贵的钱花出去,一部分给到实际项目里的支出,只留大概20%~30%覆盖人力成本。筹款上感觉被扼住了脖子。”
22:27 益微的两个十年进化:从大学生支教1.0到乡村夏令营2.0
“1998到2002年,西北师范大学的学生骑行中国,拍了很多中国西部农村的真实图片。之后他在北京做了场高校图片展,一下子点燃了主流高校的热情。那时候大家会有一种宏大叙事感,认为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乡村,还有没有桌椅的学校?我作为一个天之骄子,想去贡献一份力量。”
“在那场营会上,我见证了益微青年的诞生。冥冥之中有种命运的齿轮被拨动的感觉,我看到孩子呱呱坠地,就想陪孩子多走几步,所以一直陪伴益微青年到现在。”
“参加乡村夏令营后,你的底层信念会发生变化。乡村夏令营不太强调知识改变命运,也不鼓励你非得跟孩子说,要考上大学,跟我见面,才算是成功的人生。不是。乡村夏令营更多会去做一些关于乡土、运动、社会情感的事情,关于底层能力的发展,学习兴趣的激发。它重新塑造了教和学的关系,在这里我们都是平等的。”
34:16 “长大后我就成了谁?”
“Ta到大学后,那个藏宝袋一直没丢,里面珍藏着哥哥姐姐,还有同学给ta写的话。特别巧,藏宝袋的信封上印了益微青年的信息。某天ta拿出来翻看,上网搜了一下益微青年,刚好看到公众号在招募志愿者,最后报名通过,就继续参与活动了,而且服务的对象正是ta以前学校里的孩子。”
“严峻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会把你作为服务提供者,评判你的服务到不到位。我做支教,投入时间和精力,但是你好像没有给我提供特别好的教学环境。我只是来上课,但是你们还让我自己做饭,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简直不能理解。”
“这种张力会越来越大。做完洞察后,我们发现其实不只是大学,从小学教育开始,他的竞争倾向或者说目标聚焦就一直存在。我要不择手段达成目的,获得这样的机会,把别人挤下去。所以他会有更功利的诉求。”
42:59 公益传播的困境:组织都很好,但我们不知道
“刚才介绍了这么多组织,做的项目都这么厉害,我有种感受是为啥才知道呢?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处的学校、城市都很前沿,这么些年仍然不太了解。这是我的问题,他们的问题,还是社会组织的问题呢?”
“分享一组数据:大学生参与公益,60%的原因是在线下接触过相关信息。比如宣讲会或者是同学介绍,这是转化率最高的渠道。反倒线上可能就是10%~20%的转化率。”
“报名公益之前,大家非常在意的一点就是安全和靠谱。你这组织会不会把我送到一个地方,乱收钱,甚至让我身陷危机。对于没听说过的组织一视同仁,我都要了解一下你算不算靠谱。靠谱的定义就是有没有国家、政府、高校的背书。他们现在信息更多,选择反倒更窄了。”
52:40 受助群体“鄙视链”:老人、小孩、妇女优先,而青年排在动物之后?
“之前我们做行业扫描,当时有乡村夏令营项目的组织大概有七十多家。现在再做扫描就只剩三四十家了,近乎腰斩。因为这是一个重线下的项目,人力投入比较多,但是吃力不讨好。由于资金链断裂,或者创始人有其他的发展,就流失掉一部分。”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受助对象的选择就会有所倾斜。比如在城市和乡村肯定选乡村。乡村里的老人、小孩,妇女,接着是动物,青年排在动物之后。而金融青年还要排在青年之后。”
“现在的大学生我们定义为生命力受损。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所有的教育压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然后大学高中化,又面临这么大的就业压力,承担这么多的社会期待以及自我生存的期待。甚至现在大家会觉得啃老就是最省钱的办法。”
01:02:05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青年“非优势群体”?
“有些人会认为既然我做了公益,你就应该帮我。你不帮我就是你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如果有这种思想和意识,别人会有被道德绑架之感,为什么要帮你?”
“最终我看到很多青年社会组织,有的变成了社会企业,甚至变成商业机构,比如广州的xxxx。你们益微青年有想过朝那个方向或者领域去发展、变革吗?”
“公益要激发参与,然后建立信任。我们设计机制,让第三方愿意为这件事情买单,参与进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让大家看到我参与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承担这个成本,但是有什么样的资金流主动帮我承担了成本。而在过程当中我贡献了什么,以及收获了什么。这会是一个更加健康的参与状态。”
01:08:59 公益组织的共识:孤独、无力与希望
“今年痛定思痛了,我们得在当下做出一个清醒的认知,就是怎么让这件事情更可持续下去。现在无论是筹款量还是参与率都在逐年下滑,我们真的危机感很强。”
“在既有手段上要做一些怎样的迭代,可能是更轻量级,或者是更能满足功能性需求的调整。我们确实更强调情感性的联结,比如社交、成长、领导力提升。”
“梁晓燕老师是中国公益领域教母级别的角色,她同时做环保和教育领域。她有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做环保会更有无力感,因为你没办法单一解决整体环境问题。但是做教育反倒是很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个体。你不一定影响了100、1000万人,但是你对一个人的生命,会有这样的点燃或影响。”
-关于大力如山-
券业最野自媒体、原券商投行业务条线董事总经理、畅销书《投行职业进阶指南:从新手到合伙人》作者。创建了公益组织:金融职业发展专项基金
【每周直播预约及回看】
视频号:大力如山
【互动平台】
微信公众号:大力如山
微博@王大力如山
小红书:大力如山
【书籍】《投行职业进阶指南》(各大购书网站均有售)
评价...
空空如也
小宇宙热门评论...

unknown_cc
3个月前
上海
2
所以金融青年debuff叠满?🤔

大力如山
3个月前
上海
2
今天这期播客的嘉宾:强子(李强 益微青年总干事),不仅是我的九期班同学,还是我所在小组的同学,而他虽然是比我年轻的90后,却还是大学一毕业就加入益微做了十几年青年公益的“前辈”。我一认识强子后就挺羡慕他的,20多岁的时候就走上了我快40岁才走上的道路,跟他相比我总觉得是自己多走了20年弯路,所以真的特别好奇他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啥家庭啥背景啊?

小歪qaq
3个月前
上海
1
收获满满!

HD964417z
3个月前
江苏
1
听着听着的心路历程:
金融青年的顺序排在青年之后,的确……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金融青年一点都不是足够弱势的群体(当时讨论到这一点的时候微微破防了)[裂开]
强子老师的从1.0版本开始就刷新认知了 十几年前就已经做得那么好了,现在更是了,牛逼!
怎么看下来我们最大的优势还是有钱/敢想敢干[捂脸](力哥说是擅长瞎花钱),其实有很成功的公益组织已经趟过河了,我们现在要摸着他们过河(谨记!下次也必须会花钱!)
青年群体的生命力受损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死气沉沉的,没有活力也不愿意参加什么活动,整个都是非常的压力焦虑,被控制着长大的,然后要面临很激烈的竞争,用尽全力只是为了不被淘汰。一整个都是活人微死,阳气被吸干,但其实他们内心并不是没有活力,只是这些活力。是被压抑的,是被压制的。对照来看,他们可能会在某些领域比较疯狂,比如追星,比如游戏等等,我感觉这个好像是这个时代青年人面临的很大的议题,空心病空心人,没有活力死气沉沉
公益是适合大学生从零开始零基础低成本的,有足够空间的试错和提升自己的途径,这个我非常的赞同!未来朝这个方向努力!

拽拽喵
3个月前
甘肃
1
夯大力老师终于更新了。👏👏😄

榕榕_4SN4
3个月前
上海
1
金融青年不如狗😂😂😂感谢力哥“一陆有力”的收留,总算找到组织了!!!

大力如山
3个月前
上海
0
听得很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