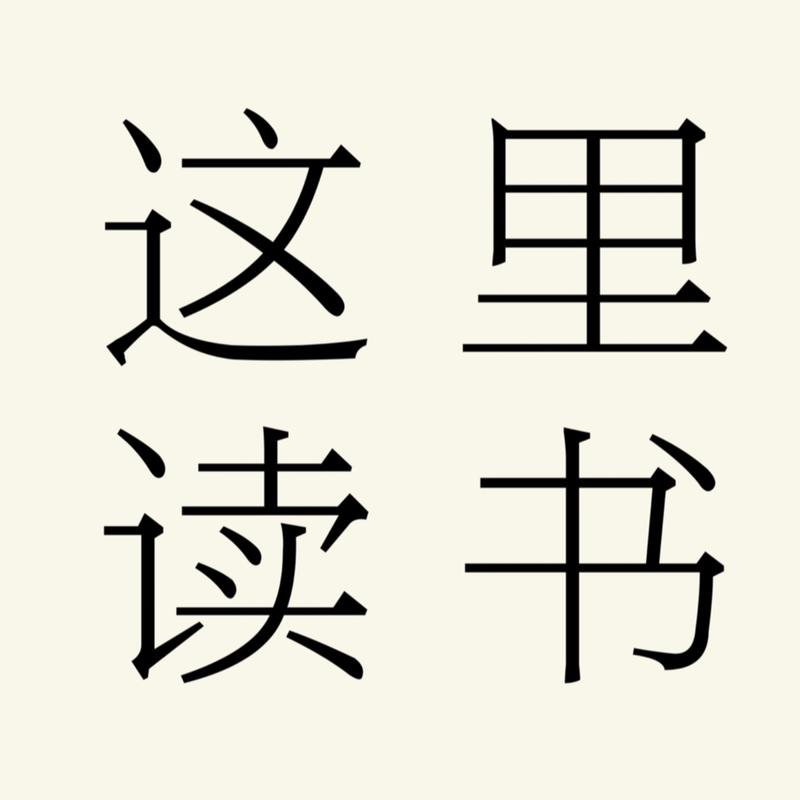
时长:
16分钟
播放:
1.08万
发布:
2年前
主播...
简介...
今天想要分享的是毛姆于1925年出版的《面纱》。这本小说是毛姆唯一一部将故事情节设定在中国的长篇小说。1919-1920年,毛姆和同性友人杰拉德·哈克斯从香港、到上海、一路北上到北京。这次旅行回来后,毛姆写下了这本小说。
原版书名The Painted Veil,源于两百年前,一首雪莱写的十四行诗「"Lift not the painted veil which those who live / Call Life".不要揭开这华丽的面纱,它被活着的人称之为生活」。
说到雪莱,这位英国的抒情诗人最被人所知的就是那首「西风颂」,里面那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让不少身处低谷的人,感到希望激励。我最近在读的另一本讲诗的书提及了雪莱,有机会以后可以分享。
回到《面纱》这部小说。小说的两位主角都是英国人。吉蒂,一个被宠坏的社交名媛嫁给了她并不爱的细菌学家沃尔特。吉蒂跟着沃尔特来到了香港,并在香港有了外遇。沃尔特为了惩罚她,给了她两个选择。一个是离婚,但是要让外遇的对象唐森娶她为妻。唐森拒绝了,因为他和吉蒂在一起,只是满足自己的肉欲,他更看重自己的妻子能够带给他的体面和支持。因此,吉蒂只剩下沃尔特给她的另一个选项,那就是跟他一起进入霍乱肆虐的湄潭府,一方面沃尔特可以凭借一己之长个治病救人,更重要的是,他也可以以此惩罚了出轨的吉蒂。
1. 【可以出轨,但不能离婚: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
这本小说在国内出版,所定下来的阅读群体很明确,就是喜欢阅读、对女性成长话题感兴趣的读者。
吉蒂在小说一开始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她漂亮得像一个演员,性格肤浅又轻浮,自相矛盾又刻薄。她的生长环境没有教给她爱和责任。
整个上流社会的风气的让吉蒂知道:女人的成功要仰赖一个男人。所以她只需要不停的社交、打球、跳舞、晚宴,然后找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嫁了。在当时,这是很典型的欧洲中上层社交名媛的生活方式。因此,当她嫁给沃尔特的时候,不是因为她爱这个男人,而是她年纪稍大,小她近10岁的妹妹,也刚刚订婚。吉蒂迫切的想要结婚,她不希望让别人觉得自己是没有归宿的老处女,因而草草嫁给沃尔特。
1910年,英国的离婚率是0.2%,在当时,女性婚后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提出离婚。即便在1923年新的《婚姻诉讼》法律颁布,女性也仅在丈夫通奸的情况下,并且要提供足够的证据才能提出离婚诉讼。
能够出轨、但不能离婚。这样的社会束缚不仅仅发生在吉蒂和沃尔特之间,也发生在查理唐森和唐森太太之间。即使唐森太太深知查理外遇不断,她仍要保持体面。甚至无法痛恨唐森先生,而只是嫉妒着唐森拥有的女友们,这种嫉妒以一种更为「体面」的方式发泄出来,那就是轻视。小说里写道「她愿意跟查理爱上的那些可怜女子交朋友;只是那些女人都太普通了。她说爱上她丈夫的搜是一些庸俗女子,着让她的脸上都觉得不是那么光彩」。
男女在婚姻关系中存在不对等的状况,这一现实是小说的背景。
1. 【死的是条狗:讲爱情,但讲的是灵魂】
小说不仅写的是爱情,甚至可以说,直至沃尔特生命的终结,吉蒂也并没有爱上沃尔特。她只是透过沃尔特灵魂里高尚的那一面,看清了曾经的自己。
等到吉蒂抵达湄潭府,她见到了留在当地救治灾民的修女,她从修女身上看到了敬畏和神圣的东西,与此同时,修女们在吉蒂面前赞美沃尔特在前线的奋不顾身。她意识到身为细菌学家、医学博士的沃尔特是这里唯一的希望,这个时候,她看到的不再是自我的情欲,而是灵魂。在极端的环境中生活,使吉蒂看到浮在表象下真正高贵的东西——不是完美的脸蛋、肌肉、更高的社会地位、能够在社会上游刃有余的圆滑世故;是不屈服、是真实的教养、是救人的能力和责任感。她看到霍乱中。亲眼看到一条条人命消失,看到在死神手中抢回生命的修女还有丈夫,让她觉得自己也需要成为一个有灵魂的人。
借此,吉蒂投入了教会的救治工作里,她觉得过往的事情都对她而言不再重要了;曾经的她,被查理·唐森背叛、抛弃之后,觉得心如死灰,也开始轻视自己的生命;但是她现在有更重要的使命需要她去完成。
也因此,一部分人在《面纱》里读到的是女性成长,这也是小说中文版本的营销方向。可以看到书的腰封就写的是「被时代裹挟的女性,从美丽且愚蠢,到拒绝诱惑、不被依附、找到自我」。
在沃尔特后来感染了病毒,在他去世前,对吉蒂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死的是条狗」。这是源于戈德·史密斯《挽歌》里的最后一句。讲的是人和狗是好朋友,有一天狗疯了,把人咬伤了。大家都担心人会死掉,但是死掉的却是那条狗。这句话在原文中没有被很清晰地阐明,为什么沃尔特会留下这样一句话。我看到有一个评论时说:狗虽然发疯,咬了人,但是实际上那个人才是有毒的,是伪善的,只不过别人看不见。人身上的毒,毒死了狗。这一个解释在我看来是不准确的。
事实上在整本小说里,「人狗」的关系都存在着,也在变化着。也是在小说开始的时候,沃尔特是那个「人」,而吉蒂是「狗」。他们相知相识,直到吉蒂出轨了查理·唐森,地下恋情被沃尔特发现,沃尔特感觉自己受到了背叛,被吉蒂咬了。因爱生恨的沃尔特决定带吉蒂去湄潭府赴死,在这里,他俩的角色由调换过来。心中满是仇恨的沃尔特一开始也许想让吉蒂死于霍乱,也应证了「疯狗咬人」的情节。但沃尔特没有意料到是,吉蒂在这个像炼狱一样可怕的湄潭府中,揭开了生活的面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拥有了人的灵魂;被爱和恨吞噬的沃尔特,最终成为了死去的狗,死前说出的「死的是条狗」,也是一种绝望的讽刺。
高贵的灵魂未必会一直高贵下去,卑劣的灵魂也有幡然醒悟的时刻。
而即小说有趣的地方在于,即使灵魂可以变得高贵起来,也可以复杂的具有卑劣的属性。吉蒂成长后开始鄙夷曾经那个轻浮的自己,但当她再次回到香港时,仍然没有办法抵抗查理·唐森对她的爱欲。
正如雪莱的诗里所写:生活的面纱总是用各种形式来迷惑着芸芸众生,如何揭开这样的面纱,是这本小说的主题。
1. 【小说的缺陷——不完整的东方背景】
最后来简单聊一下小小的批判,或者说是critical thinking/客观分析。毛姆在西方文坛,尤其是20世纪小说世界里被人列入二流的小说家。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经历着剧烈的变革。他们或者可以反应现实,或者需要超出现实;或者通过意识流的形态写出,或者以象征性叙述,将抽象的思想、意识知觉化、具像化。譬如日后会讲到的卡夫卡就是这一流派的典型作者。毛姆的自然派写法,线性的叙述,以及视角的稳定,使得小说缺乏实验性,更像是一个传统小说。补过,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缺点。
真正让我感到失落的,是他对于异国情调的描写。他从1919年8月到1920年4月之间,曾深度探索中国,但是他并不会讲中文,在旅行过程中观察的视角也很少聚焦在士民阶层。《面纱》这部小说所写的也几乎是中国土地上殖民者的生活,唯一提到的两个中国角色,治理霍乱的于团长,甚至连台词也没有,另一个则是满洲的格格,她放弃了地位和家庭,选择嫁给英国来的海关下属官员韦丁顿。关于满洲格格的描写,毛姆也有一些遮掩,仿佛雾里看花,水中看月。这让我能够理解,也许毛姆在中国的旅行中,语言的不通,文化背景的巨大区别,使他终归觉得无法下笔深入写任何一个东方角色。于是东方背景,仅仅成为了异域情调,而不是滋养整个故事发生的土壤。因此,在读《面纱》时,我感觉到了某种缺失。前几年的电影翻拍中,似乎努力想要弥补小说里的桥段,给予了于团长更立体的形象,甚至对于国人的描写也更鲜明了。
最后,我尝试着读了几页英文原版,个人觉得我手中王晋华的版本翻译的很好。毛姆本身的语言也很简洁干练,可能对于想要坚持英文原版阅读的人来说,不会太困难。希望大家能够享受阅读这本书。
*原文中喜欢的一段。Kitty吉蒂对沃尔特表示,沃尔特对吉蒂的要求是不公平的,说她轻佻、愚蠢是不公平的。因为她所生长的环境就是这样教导她的,所有的女孩都是这样被抚养长大。不知道为什么,这段对话让我想到了波伏瓦对于女性成长环境的看待。
“I think you do me an injustice. It’s not fair to blame me because I was silly and frivolous and vulgar. I was brought up like that. All the girls I know are like that…It’s like reproaching someone who has no ear for music because he’s bored at a symphony concert. Is it fair to blame me because you ascribed to me qualities that I hadn’t got? I never tried to deceive you by pretending I was anything I wasn’t. I was just pretty and gay. You don’t ask for a pearl necklace or a sable coat at a booth in a fair; you ask for a tin trumpet and a toy balloon.”
原版书名The Painted Veil,源于两百年前,一首雪莱写的十四行诗「"Lift not the painted veil which those who live / Call Life".不要揭开这华丽的面纱,它被活着的人称之为生活」。
说到雪莱,这位英国的抒情诗人最被人所知的就是那首「西风颂」,里面那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让不少身处低谷的人,感到希望激励。我最近在读的另一本讲诗的书提及了雪莱,有机会以后可以分享。
回到《面纱》这部小说。小说的两位主角都是英国人。吉蒂,一个被宠坏的社交名媛嫁给了她并不爱的细菌学家沃尔特。吉蒂跟着沃尔特来到了香港,并在香港有了外遇。沃尔特为了惩罚她,给了她两个选择。一个是离婚,但是要让外遇的对象唐森娶她为妻。唐森拒绝了,因为他和吉蒂在一起,只是满足自己的肉欲,他更看重自己的妻子能够带给他的体面和支持。因此,吉蒂只剩下沃尔特给她的另一个选项,那就是跟他一起进入霍乱肆虐的湄潭府,一方面沃尔特可以凭借一己之长个治病救人,更重要的是,他也可以以此惩罚了出轨的吉蒂。
1. 【可以出轨,但不能离婚: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
这本小说在国内出版,所定下来的阅读群体很明确,就是喜欢阅读、对女性成长话题感兴趣的读者。
吉蒂在小说一开始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她漂亮得像一个演员,性格肤浅又轻浮,自相矛盾又刻薄。她的生长环境没有教给她爱和责任。
整个上流社会的风气的让吉蒂知道:女人的成功要仰赖一个男人。所以她只需要不停的社交、打球、跳舞、晚宴,然后找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嫁了。在当时,这是很典型的欧洲中上层社交名媛的生活方式。因此,当她嫁给沃尔特的时候,不是因为她爱这个男人,而是她年纪稍大,小她近10岁的妹妹,也刚刚订婚。吉蒂迫切的想要结婚,她不希望让别人觉得自己是没有归宿的老处女,因而草草嫁给沃尔特。
1910年,英国的离婚率是0.2%,在当时,女性婚后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提出离婚。即便在1923年新的《婚姻诉讼》法律颁布,女性也仅在丈夫通奸的情况下,并且要提供足够的证据才能提出离婚诉讼。
能够出轨、但不能离婚。这样的社会束缚不仅仅发生在吉蒂和沃尔特之间,也发生在查理唐森和唐森太太之间。即使唐森太太深知查理外遇不断,她仍要保持体面。甚至无法痛恨唐森先生,而只是嫉妒着唐森拥有的女友们,这种嫉妒以一种更为「体面」的方式发泄出来,那就是轻视。小说里写道「她愿意跟查理爱上的那些可怜女子交朋友;只是那些女人都太普通了。她说爱上她丈夫的搜是一些庸俗女子,着让她的脸上都觉得不是那么光彩」。
男女在婚姻关系中存在不对等的状况,这一现实是小说的背景。
1. 【死的是条狗:讲爱情,但讲的是灵魂】
小说不仅写的是爱情,甚至可以说,直至沃尔特生命的终结,吉蒂也并没有爱上沃尔特。她只是透过沃尔特灵魂里高尚的那一面,看清了曾经的自己。
等到吉蒂抵达湄潭府,她见到了留在当地救治灾民的修女,她从修女身上看到了敬畏和神圣的东西,与此同时,修女们在吉蒂面前赞美沃尔特在前线的奋不顾身。她意识到身为细菌学家、医学博士的沃尔特是这里唯一的希望,这个时候,她看到的不再是自我的情欲,而是灵魂。在极端的环境中生活,使吉蒂看到浮在表象下真正高贵的东西——不是完美的脸蛋、肌肉、更高的社会地位、能够在社会上游刃有余的圆滑世故;是不屈服、是真实的教养、是救人的能力和责任感。她看到霍乱中。亲眼看到一条条人命消失,看到在死神手中抢回生命的修女还有丈夫,让她觉得自己也需要成为一个有灵魂的人。
借此,吉蒂投入了教会的救治工作里,她觉得过往的事情都对她而言不再重要了;曾经的她,被查理·唐森背叛、抛弃之后,觉得心如死灰,也开始轻视自己的生命;但是她现在有更重要的使命需要她去完成。
也因此,一部分人在《面纱》里读到的是女性成长,这也是小说中文版本的营销方向。可以看到书的腰封就写的是「被时代裹挟的女性,从美丽且愚蠢,到拒绝诱惑、不被依附、找到自我」。
在沃尔特后来感染了病毒,在他去世前,对吉蒂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死的是条狗」。这是源于戈德·史密斯《挽歌》里的最后一句。讲的是人和狗是好朋友,有一天狗疯了,把人咬伤了。大家都担心人会死掉,但是死掉的却是那条狗。这句话在原文中没有被很清晰地阐明,为什么沃尔特会留下这样一句话。我看到有一个评论时说:狗虽然发疯,咬了人,但是实际上那个人才是有毒的,是伪善的,只不过别人看不见。人身上的毒,毒死了狗。这一个解释在我看来是不准确的。
事实上在整本小说里,「人狗」的关系都存在着,也在变化着。也是在小说开始的时候,沃尔特是那个「人」,而吉蒂是「狗」。他们相知相识,直到吉蒂出轨了查理·唐森,地下恋情被沃尔特发现,沃尔特感觉自己受到了背叛,被吉蒂咬了。因爱生恨的沃尔特决定带吉蒂去湄潭府赴死,在这里,他俩的角色由调换过来。心中满是仇恨的沃尔特一开始也许想让吉蒂死于霍乱,也应证了「疯狗咬人」的情节。但沃尔特没有意料到是,吉蒂在这个像炼狱一样可怕的湄潭府中,揭开了生活的面纱,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拥有了人的灵魂;被爱和恨吞噬的沃尔特,最终成为了死去的狗,死前说出的「死的是条狗」,也是一种绝望的讽刺。
高贵的灵魂未必会一直高贵下去,卑劣的灵魂也有幡然醒悟的时刻。
而即小说有趣的地方在于,即使灵魂可以变得高贵起来,也可以复杂的具有卑劣的属性。吉蒂成长后开始鄙夷曾经那个轻浮的自己,但当她再次回到香港时,仍然没有办法抵抗查理·唐森对她的爱欲。
正如雪莱的诗里所写:生活的面纱总是用各种形式来迷惑着芸芸众生,如何揭开这样的面纱,是这本小说的主题。
1. 【小说的缺陷——不完整的东方背景】
最后来简单聊一下小小的批判,或者说是critical thinking/客观分析。毛姆在西方文坛,尤其是20世纪小说世界里被人列入二流的小说家。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经历着剧烈的变革。他们或者可以反应现实,或者需要超出现实;或者通过意识流的形态写出,或者以象征性叙述,将抽象的思想、意识知觉化、具像化。譬如日后会讲到的卡夫卡就是这一流派的典型作者。毛姆的自然派写法,线性的叙述,以及视角的稳定,使得小说缺乏实验性,更像是一个传统小说。补过,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缺点。
真正让我感到失落的,是他对于异国情调的描写。他从1919年8月到1920年4月之间,曾深度探索中国,但是他并不会讲中文,在旅行过程中观察的视角也很少聚焦在士民阶层。《面纱》这部小说所写的也几乎是中国土地上殖民者的生活,唯一提到的两个中国角色,治理霍乱的于团长,甚至连台词也没有,另一个则是满洲的格格,她放弃了地位和家庭,选择嫁给英国来的海关下属官员韦丁顿。关于满洲格格的描写,毛姆也有一些遮掩,仿佛雾里看花,水中看月。这让我能够理解,也许毛姆在中国的旅行中,语言的不通,文化背景的巨大区别,使他终归觉得无法下笔深入写任何一个东方角色。于是东方背景,仅仅成为了异域情调,而不是滋养整个故事发生的土壤。因此,在读《面纱》时,我感觉到了某种缺失。前几年的电影翻拍中,似乎努力想要弥补小说里的桥段,给予了于团长更立体的形象,甚至对于国人的描写也更鲜明了。
最后,我尝试着读了几页英文原版,个人觉得我手中王晋华的版本翻译的很好。毛姆本身的语言也很简洁干练,可能对于想要坚持英文原版阅读的人来说,不会太困难。希望大家能够享受阅读这本书。
*原文中喜欢的一段。Kitty吉蒂对沃尔特表示,沃尔特对吉蒂的要求是不公平的,说她轻佻、愚蠢是不公平的。因为她所生长的环境就是这样教导她的,所有的女孩都是这样被抚养长大。不知道为什么,这段对话让我想到了波伏瓦对于女性成长环境的看待。
“I think you do me an injustice. It’s not fair to blame me because I was silly and frivolous and vulgar. I was brought up like that. All the girls I know are like that…It’s like reproaching someone who has no ear for music because he’s bored at a symphony concert. Is it fair to blame me because you ascribed to me qualities that I hadn’t got? I never tried to deceive you by pretending I was anything I wasn’t. I was just pretty and gay. You don’t ask for a pearl necklace or a sable coat at a booth in a fair; you ask for a tin trumpet and a toy balloon.”
评价...
空空如也
小宇宙热门评论...

咸鱼罐头
2年前
美国
19
刚看完,没有感觉到沃尔特有爱人的能力,他那段最有名的告白也充满了对凯蒂的贬低,说到底他只是爱上了凯蒂的皮囊,并执意把她奉为女神。当发现凯蒂出轨承载不了他那满腔的“爱意”就判若两人。凯蒂是有弧光的,若说品质她更善良,后期还一直想帮沃尔特解开心结。在我看来这不是个爱情故事,而是如何找到自我的故事,毛姆更想写结构性的压迫而不是谈情说爱。

小萨桃路易茶
2年前
浙江
8
睡前听桃酱,突然有种拨开面纱、抬头望月的畅快!缓解了我的焦虑,晚安~桃酱~

馨怡_qHVp
2年前
河北
4
桃酱桃酱你看的这本面纱是谁翻译的,这对我很重要

不想熬夜精
1年前
天津
2
桃酱讲的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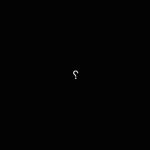
HD234779z
2年前
浙江
1
睡前听刚好!

咸约翰
2年前
北京
1
晚安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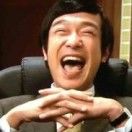
記憶力不行
1年前
广东
1
头一回读,觉得毛姆太刻薄了,女主回到香港还要被欲望征服。第二次读,只觉得揭开面纱只有两个字,生和死。死亡那么远那么近,即便女主浅薄也意识到这个主题下沉重的叩问。而生,就是爱欲烦忧,没有了那些爱欲烦忧,生也如同死去。女孩父亲看到女儿好像老了五十岁,就像看到女儿的生命力在被抽走。我严重怀疑毛姆内心中就是个女人

帕格桃桃
1年前
福建
1
11:02 感谢桃酱对“人和狗”的故事做了补充,一个人读的时候确实有点理解不了🤔

停云蔼蔼_dXXE
1年前
湖南
1
00:49 这里念的英文好好听啊!

mo_VhlQ
1年前
广东
1
是裹挟xie呢桃酱🍑

鱼游水77
1年前
浙江
0
好爱睡前听

林慕江
1年前
四川
0
听了桃酱的播客准备去看看这本书🤩

甜桃酱
1年前
北京
0
看完书后,再听一遍桃酱的解读~~

猛猪猪小桃
1年前
北京
0
桃酱快点更新吧呜呜呜,反反复复的听这里读书的节目,已经沉迷🍑的声音了哈哈哈哈😆

夏天西兰花盖饭
1年前
广东
0
很喜欢毛姆写的小说

jancy_xi
1年前
湖北
0
哈哈哈哈听到最后才发现是桃酱!

Cell_Xk7w
1年前
陕西
0
感谢分享,但是桃酱啊,更新的频率有点低呀😞

HD82320t
10个月前
山东
0
这个表白好像是kitty对唐生说的?

金梦蕊
10个月前
河南
0
讲得太棒了!

Shadow_SnMc
8个月前
河南
0
书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一个男人可以很爱一个女人,但同时并不想与她共度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