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光临五点起床,五点起床是一个和大家共读成长的频道。通过每天清晨二十分钟的阅读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 improving little by little everyday。今天和大家分享25本年度书单中的第二本——《多谈谈问题》
吴琦
困难的不是回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这种行为本身就蕴含了抗拒、反对和不甘。在动荡的年头,这是一种维持基本尊严的方式,即便它会延宕人的痛苦,但至少我们不再对痛苦的根源视而不见。
活在问题中
这些年医学取得了哪些重大进展?
什么是好的工作?未来还需要工作吗?
如何主动获取知识,而不是生存在算法中?
如何限制权力,并拒绝成为其附庸?
应该建立怎样的历史意识?
下沉年代,保持乐观积极还有什么用?
所谓Z世代,到底是怎样的一代?
人类会被环境危机吞噬吗?社会对未来还有理想吗?
知道锺叔河这个名字,来自“走向世界”丛书。它像是20世纪80年代的某种象征,一个解冻的社会,急于反省过去,想象未来,了解外部的一切。一个湖南人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他将一个多世纪前中国人的海外见闻编辑成书,提供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图景:原来在那个被描述为停滞、保守的年代,一些中国人已这样描述了世界的面貌,带着同样的困惑与惊奇。
中国现代的变化就是太快了。物理学上有一个东西叫作波,波的波峰和波谷之间高度相差很大,但是我们的波段被压缩得很短,别人正常几百年完成的过渡时期,我们把它压缩到几十年,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很多不正常的现象。
提问:我想问一下锺先生,我会感觉这两年我自己、还有好多我的朋友们好像都会有一种无力感,面对一些事情或者是整个世界的变化,好多事情你觉得不对,但是好像又确实没什么对策。锺:我有一个基本观点,社会的文明和社会的开放的程度,毕竟还是在慢慢进步的。但是我们这个国家正因为传统悠久,有可以自傲的传统文明,所以它的保守性也是特别强的,我们走向全球文明的道路会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使所有人的思想现代化起来。讲起来会发现,有人觉得读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的人的思想当然是现代化的思想,那不见得,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此,不一定。
提问:今天我主要想讨论一下媒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互联网诞生以来,已经肉眼可见地全面改写了人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描述这种影响?又应该怎么应对?比如之前我们谈到网暴,网暴变得轻易、随时都可能发生,我觉得似乎已经存在一种网络人格,它和现实世界的人格不同……这种分裂也好,互相影响也好,应该怎么去看?
戴:互联网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但你最后提到的现象,倒可以成为我们的切入点。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美国奥斯卡——因为奥斯卡作为好莱坞的主秀场,会显现出诸多好莱坞-美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与精神症候。今年,我在看德尔·托罗(“陀螺”,Guillermo del Toro)重拍的《玉面情魔》(Nightmare Alley)之前,先读到了一份他的访谈,有意外的收获。他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我们整体地陷入了认识论危机。他用了“认识论危机”这样的表达,描述今日的互联网结构(我猜是指大数据、精准投放、推送——信息茧房)令我们无法从互联网上获取新知、发现未知,甚至丧失了求知的意识和愿望。经由网络、经由传播,我们只会印证自己的已知,确信自己的正确,因此我们无从形成新观点,丧失了质疑既有观点和立场的可能性。
郭:这的确和早期人们对互联网的想象不一样,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认为通过数据库、搜索引擎,我们可以更自由、更便捷、更迅速,拥有此前无法想象的海量信息。当然也有很多人质疑,它真的让人更自由了吗?
戴: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中,互联网都的确是一个越来越丰饶的“宇宙”。经由渐次完备的数据库与搜索引擎,人们似乎已具备了自主学习、获取知识的硬件环境。然而,搜索引擎的设计已然包含了酿造“认识论危机”的因素。尽人皆知,互联网搜索引擎的使用,取决于关键词的设置与选取。作为密语与密钥,它是召唤出互联网贮藏和打开网络世界的起始。在此同样暂时不去讨论“关键词”的设置,检索对整个教育制度、知识生产产生的多重影响,仅就我们的议题而言,你既有的知识结构、趣味、诉求先设了关键词的选取,关键词则召唤、打开你兴趣、关注所在的世界。理论上,经由数据库、搜索引擎,你可以拥有整个宇宙,但事实上,你从互联网的黑洞、黑海中能够召唤出来的,是你已知并获得了召唤意愿的所在,而不会不期而遇、自主显现。
并非保守主义怀旧:在纸媒时代,你浏览报刊,当然置身于决定版面设计、栏目分布的大的权力结构,但你仍随时可能与未知、新知遭遇;一如你漫步书店会发现不流行、尚无口碑的新书……而在互联网上,尤其是当分众状态形成,资本主导的大数据、精准投放开始之际,类似的可能已全然丧失。
理论上我们获取并持有了全部旧媒体以及它们曾负载的文本、内容,但坍缩同时伴随着溶解。更重要的是,在这界面之上海量的、无法穷尽、人力难于计数的信息、影像使你无从感知到你拥有、行使的近乎无限的选择权其实是被先行选择的真相。
我以为,这三方面:分众、信息茧房/精准投放(其间、其后的是硕大赤裸的资本的主导性力量)、闭锁之宅与心理舒适带,造就了社会生存的新情态,也造成了“陀螺”所谓的“认识论危机”。疫情的发生和延续全方位地加剧了这一状态。长时段的隔离、封控,一方面造成了普遍的忧郁、焦虑,另一方面则是“宅”的常态化和结构化;不同的是,怡然、富足、自得感在褪色,无奈、无助感在上升。似乎无所不知,却又缺少关于现状的有效信息、参数和判断——遑论行动的可能。这一切,和冷战终结后两大世界性趋势——一则是急剧的、加速度的贫富分化、阶级固化,一则是整个世界丧失了全球资本主义之外的另类选择与乌托邦冲动的全面耗竭——相伴生,累积着越来越强烈的戾气。极度消极无助的社会情绪。这无疑是连绵的网络战火、网暴的由来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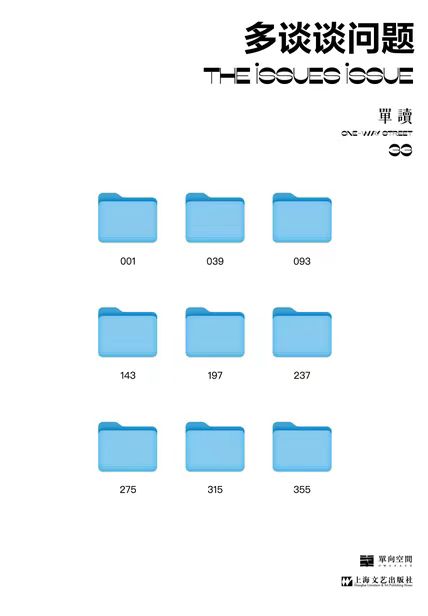
空空如也
暂无小宇宙热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