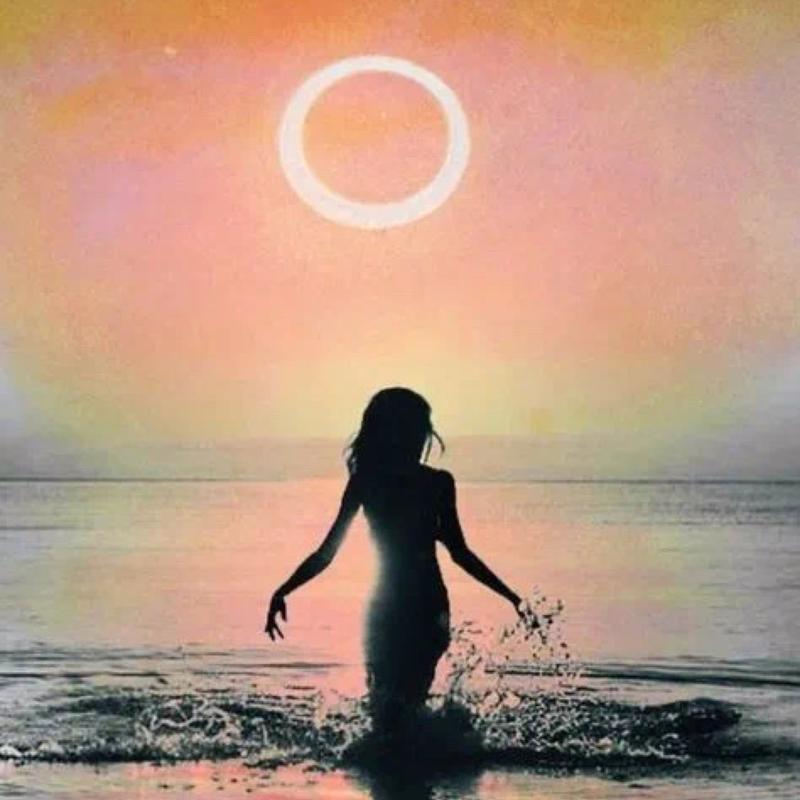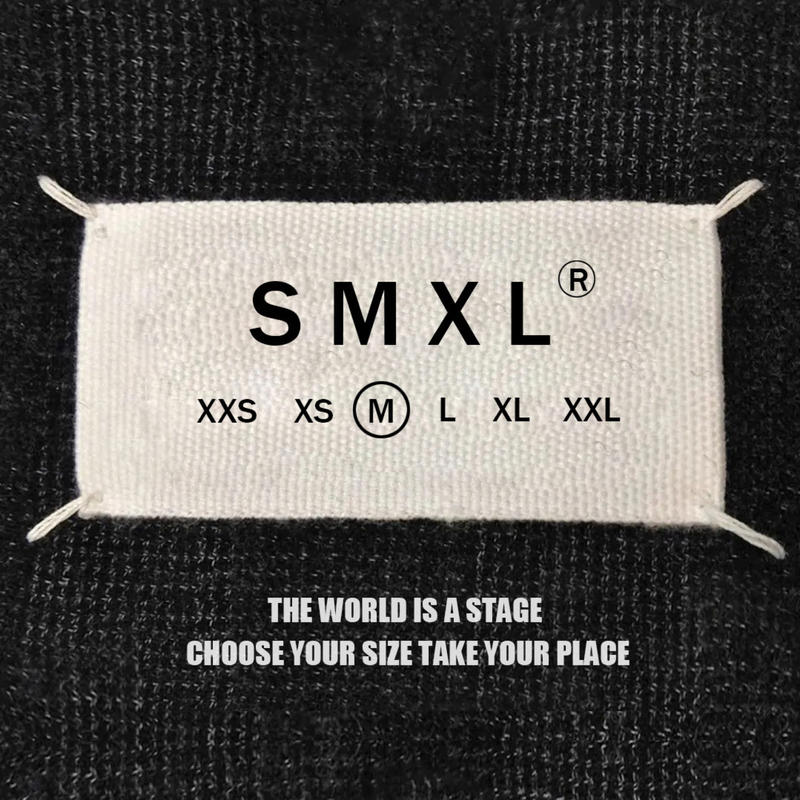
距离二月初的土耳其大地震已有一个月,国内最近也有多地发生不同震级的地震,愿多一些平安。今日惊蛰,万物苏醒,希望在人们的努力下家园的恢复顺利进行。有韧性的古老文明,不会毁于大地震。
这一期,我们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帕慕克于1952年出生在伊斯坦布尔,在这里,衰亡帝国的心酸记忆和渴望西化的强烈欲望交织。他自幼学画,大学主修建筑,后来写作,成为一个小说家。引用一句他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的第十章“呼愁”构筑了全书的基调:“呼愁”一词,土耳其语的“忧伤”,有个阿拉伯根源:它出现在《古兰经》时(两次写作“hüzn”,三次作“hazen”),词义与当代土耳其词汇并无不同。先知穆罕默德指他妻子赫蒂彻和伯父塔里布两人过世的那年为“Senetül hüzn”,即“悲伤之年”,证明这词是用来表达心灵深处的失落感。这个词构筑了整本书的基调:“我的起始点是一个小孩透过布满水汽的窗户看外面所感受的情绪。”
帕慕克曾多次公开提到,孩子般的纯真是他写作时最需要的状态。《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不失为注脚,帕慕克多年前曾在伊斯坦布尔购置一处房产,所在地正是长篇小说《纯真博物馆》里女主角芙颂家的住址,博物馆的藏品主要反映伊斯坦布尔当地的文化和城市生活,也与当代艺术家合作展示艺术和绘画。
分享书中篇章
呼愁:我所说的是太阳早早下山的傍晚,走在后街街灯下提着塑料袋回家的父亲们。隆冬停泊在废弃渡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船上的船员擦洗甲板,一只手提水桶,一只眼看着远处的黑白电视;在一次次财务危机中踉跄而行、整天惶恐地等顾客上门的老书商;抱怨经济危机过后男人理发次数减少的理发师;在鹅卵石路上的车子之间玩球的孩子们;手里提着塑料购物袋站在偏远车站等着永远不来的汽车时不与任何人交谈的蒙面妇女;博斯普鲁斯老别墅的空船库;挤满失业者的茶馆……
美丽如画的偏远邻里:让我们回想本雅明的话,他说从城外来的人对异国情调与如画之景最感兴趣。这两位民族主义作家在他们本身是外来者的地区才看得见城市的“美”。这让人想起关于日本著名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的一则故事,在对日本传统房屋予以夸赞,并以钟情的语调详细描述其建筑构造之后,他跟妻子说他决不住这种房子,因为缺少西方的舒适设施。
黑白影像:由于我是以黑白影像来理解这城市之灵魂,因此少数目光独到的西方旅人的线条素描——例如柯布西耶,以及任何一本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附黑白插图的书都令我着迷。
新版序:儿时的60年代,我就认识著名摄影家古勒,因为他拍摄的照片发表在我姨父担任主管兼首席作家的《生活》(Hayat)周刊上,因此我听到过很多关于他的故事。此外,阿拉·古勒不仅是伊斯坦布尔和整个土耳其的摄影家,从毕加索到希区柯克,他还拍摄了20世纪最优秀的创作者的美妙肖像照。1994年夏天,当他为《世界报》的副刊封面第一次来家里为我拍照时,我42岁。那天,我对自己说“这下我真的是作家了”。
生性浪漫的人,总觉得当下的时刻无聊,需要依靠阅读打开想象力之窗。
提到的书:《我的名字叫红》《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纯真博物馆》
BGM 土耳其音乐家Yildirim Gürses创作的《Gurbet O Kadar》,演奏中使用了三种传统乐器,中东乐器之王乌德琴,阿拉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卡农琴和宝思兰鼓。
空空如也
暂无小宇宙热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