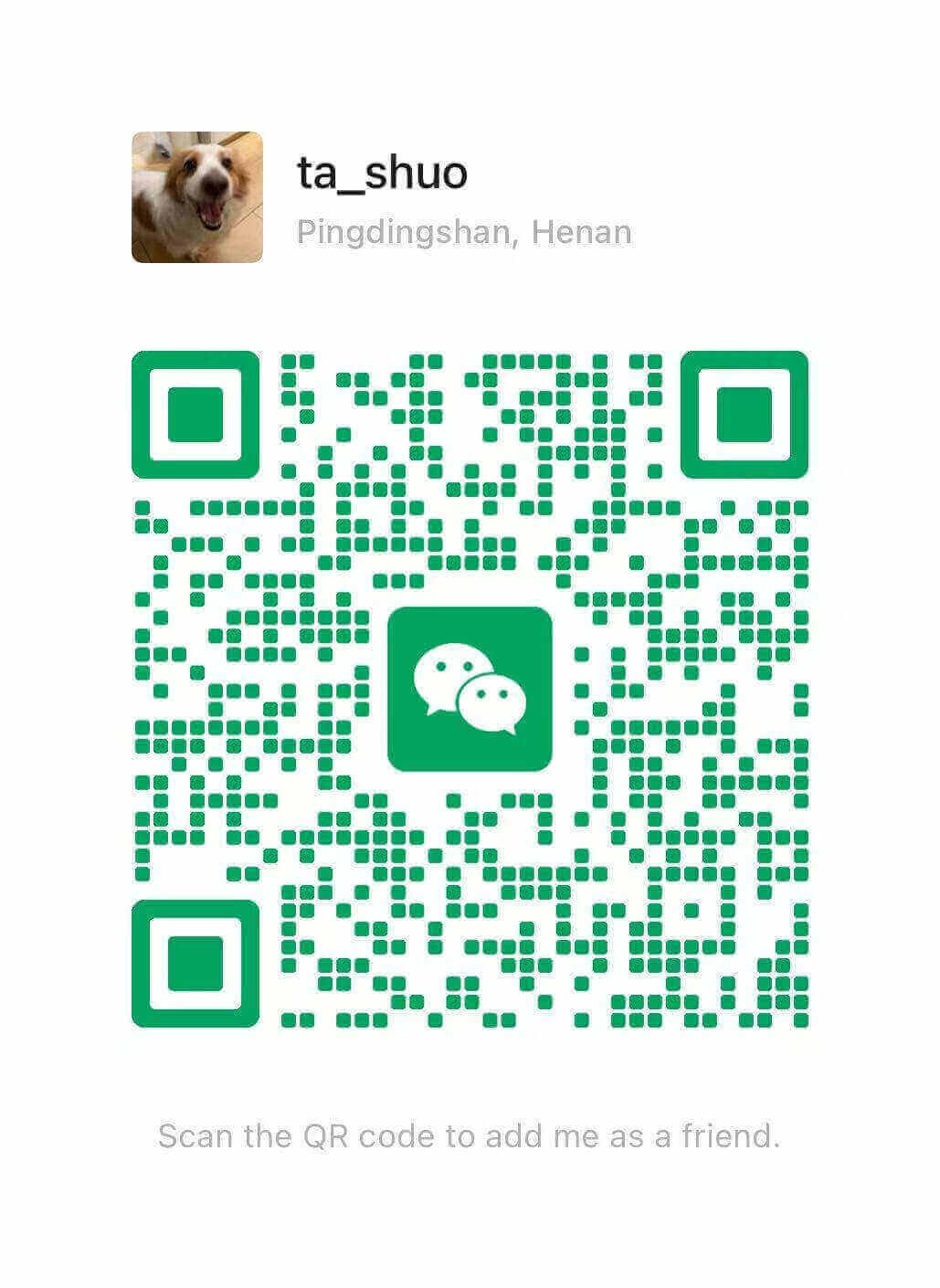文字版本请看(Echo的山海之间)
故事一开始,已经成为精英律师泰莎的自信满满、意气风发、滔滔不绝。她毕业于剑桥大学法学院,是“精英中的精英”。法学院里,只有三分之二的人能顺利毕业,十分之一能够拿到大律所的实习,五分之一会成为皇家律师……泰莎过五关斩六将进剑桥,又过五关斩六将成为律师。
这五分之一里的大多数人是贵族子弟,毕业于昂贵的私立学校。泰莎依然是例外。她出身于利物浦的贫困社区,父亲缺席,母亲是清洁工,兄长是不学无术的无业游民,家庭经济拮据。从底层社会一点点向上攀爬,泰莎对法律以及它背后的社会机制,产生了深深的崇拜。她的经历就是阶层跨越的样本,她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法律成为她的安身立命之本。
泰莎的法律崇拜,也与她成功的职业经历有关。她凭借对法律条文的熟悉、逻辑思维的敏捷、辩论技巧的出色以及长期的勤恳努力,一次次帮助她的客户赢得诉讼,包括性侵案件中的被告。她在律所里出类拔萃,并收到更顶尖律所抛出的橄榄枝。此时的她是法律体系的受益者——法律赋予她地位、权力与社会认同。她相信法律是公平和正义的象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石,只要遵循法律程序,各司其职,剩下的就是陪审团的事了。
泰莎并非没有过疑惑,比如“在明知对方犯了罪的情况下,你该如何为他辩护”。作为既得利益者,泰莎说服自己,“我们相信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所有人都是无辜的,这是维持社会文明的基本原则”“要置身事外,不要选边站”“绝不进行评判,绝对不可以,也绝不做决定!一旦做了,你就完蛋了”。特别是,在一起性侵案的辩护中,她很同情原告受害者,对方的说法“我只是不想让其他女人再受到这个男人的伤害”让泰莎震撼、钦佩,但泰莎自我“洗脑”,“我受过训练,要以律师的准则思考”“如果他(泰莎的委托人)真的性侵她了呢?我帮他脱罪了。我不能这么想,是公诉人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此刻的她,堪称法律体系的完美零件:冷静、高效,甚至“无情”,信奉正当的法律程序高于一切。
直到泰莎成为性侵案中的受害者。一次与男同事朱利安的约会,让泰莎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约会过程中,泰莎因饮酒过量而感到极度不适,在她难受呕吐后,虽然已经强烈表示出拒绝,男同事仍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是的,他强奸了她。泰莎几个小时后就选择报警,在782天后,她迎来一场必败的终审判决。
《初步举证》将泰莎的身份设置为律师,更充分地暴露出性侵案件中法律体系的漏洞,尤其是所谓的“完美受害者”就是一种苛求。
一方面,与普通的性侵受害者不同,作为一名精英律师,泰莎对法律体系有着深入的了解,她知道法律程序的每一个环节,熟知证据链的构建逻辑。当她不幸地成为一名性侵受害者,一切专业知识在创伤面前土崩瓦解,她的应对无法“完美”。譬如性侵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在酒精与恐惧的双重作用下,泰莎选择清洗身体……这个行为在司法程序中被视为“破坏证据”,但对一些受害者而言,这是原始的生存本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表现——“很多性侵犯受害者都会因为自己身上有施暴者的气味或者觉得自己很脏而有强烈的想要清洁身体的冲动,这是很正常的。”(芭芭拉·O.罗特鲍姆、希拉·A.M.劳赫《创伤后应激障碍》)当我们要求受害者冷静、理性、从容应对,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性侵创伤带来的生理应激反应与心理撕裂,很有可能摧毁受害者的理性控制能力。就像一个人明明已经溺水了,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她在激流中保持发型整齐?
另一方面,作为律师,“逻辑”是泰莎最锋利的武器。她太了解法律程序的精密齿轮如何咬合转动,她善于将复杂的人性纠葛拆解为可量化的证据链条,精准揪出证词中的矛盾点,攻破对方的防线。可当泰莎成为受害者时,当她以“法律逻辑”分析自己的经历:餐厅账单显示她与男同事喝了不少酒,餐厅的人目睹两人相谈甚欢,她主动邀请对方回家,家里有两个空的红酒瓶,她主动脱下衣服,他们此前曾发生过性关系……这些证据链让陪审团认定“合意”的存在。泰莎曾引以为傲的法律的逻辑,如今成为刺向她的利刃。
不止于此。一个性侵受害者的记忆是充满创伤的,是碎片化、情绪性、感官化的,而非连贯的、理性的、严丝合缝的。这又与法律所需的“完美逻辑”形成根本冲突。知名心理创伤治疗大师巴塞尔·范德考克的研究发现,“创伤性经验的印记和体验无法如同叙事性记忆那样组织得前后一致、合乎逻辑,而是以碎片化的感知和情绪痕迹体现:例如图像、声音、感觉”,“当他们的经历遭受质证时,受害者通常变得非常痛苦而无法说话,或者他们被惊恐所控制以至于他们不能很好地组织语言、描述他们发生过的事情。这些质证常常因为过于混乱、迷惑或者碎片化而使法庭认为不可信,从而不予考虑。”(《身体从未忘记:心理创伤疗愈中的大脑、心智和身体》)就比如泰莎能清晰记得呕吐物的酸味、被捂住嘴的窒息感,却难以准确复现施暴者的动作顺序——男同事到底是怎么一边摁住她的双手,一边捂住她的嘴巴的?受害者的证词常常因细节模糊、时间线混乱而被辩方攻击,她明明没有撒谎,却在庭审中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就算是深谙法律程序、熟稔逻辑构建的精英律师泰莎,在不幸经历性侵后,依然陷入“不完美受害者”的困局。这一设定强有力地暴露了法律体系对受害者的结构性压迫——它用冰冷的程序正义之名,要求受害者以“完美”的逻辑对抗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崩溃,本质是行性别暴力之实。我们并不排除存在所谓的“完美受害者”,但绝不能将“完美”作为衡量受害者是否值得同情与法律是否给予支持的唯一标准,这是对受害者的苛求,甚至是新的压迫。
除了指出“完美受害者”的破绽,《初步举证》也经由泰莎从工人家庭跻身精英律师的身份设定,点出一个残酷的真相:并非成为精英,就能躲避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换句话说,不幸成为受害者,并非因为不完美——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阶级跃升无法真正跨越性别压迫的鸿沟。
泰莎的逆袭之路表面上印证了“奋斗改变命运”的个体叙事,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剑桥法学院,在男性主导的律所中凭借专业能力赢得尊重。但她依然遭到侵害,曾经引以为傲的法律体系瞬间显露出系统性暴力。诚如戴锦华教授在“新现场”组织的《初步举证》首映礼的映后交流中谈到的:“我们没有好身世、没有好家世、没有好背景的女人,觉得我们可以通过奋斗,最终成为胜出者,而不是出局者。那么这个就是在说我自尊、自爱、自强、自律的同时,是不是其实也包含了对弱者,对不成功的女性,对受害者女性的某种不屑?而事实上你会发现单纯在性别这个维度上,其实大概也很难逃脱这样一个父权制度之下,身为女性的宿命。”
这一“自我反省”戳破精英女性可能陷入的认知陷阱。泰莎曾以优胜者的姿态俯视那些未能突破阶级壁垒的女性,将她们的困境归因为个体能力的不足,将父权制度下的结构性压迫简化为女性不够自律、不够自强等等。然而,在性别维度上,精英女性与底层女性一样是客体、一样有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更令泰莎感到悲哀的是,精英律师身份让她的“不完美”更加刺眼——因为她是律师,她就更被期待应该“完美”,她越是“不完美”,越被怀疑“别有用心”。她曾是这个法律体系的忠诚拥护者,也曾成为“帮凶”,它对她的反噬尤为惨痛。
苛求“完美”的体系是偏狭的
回想起来,每当一些性侵案件登上社会新闻时,舆论往往陷入一种诡异的循环:很多人热衷于教导女性如何避免受害——不要独自夜行、不要饮酒过量,抑或如果不幸遭遇伤害后,应该如何理性冷静地保留证据。这些说法不见得是错的,出发点也是因为关切,却将责任悄然转嫁给受害者。
追根究底,我们期待女性面面俱到地自我保护、期待受害者“完美”,表面上是希望法律能够保护受害者,但其实我们是在以法律的程序和逻辑要求受害者。因为法律要求女性在遭受性侵后提供近乎完美的证据,就像泰莎说的“法律要求证据要维持一致”,所以我们就反复“教导”女性按照法律说的做,否则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这个逻辑看上去是如此顺理成章、无懈可击。《初步举证》则进一步追问:法律就是完美的吗?法律代表的是谁的立场和视角?如果说法律就是绝对正义的,为何在性侵案件中,现有的法律体系与女性的生存经验背道而驰?正如泰莎指出的,“作为一名受害者,我要说的是,性侵和施暴者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但我们记不清细节”,性侵不同于其他犯罪,它对受害者的心理和身体造成的创伤是极其深远的,或导致记忆的混乱、情绪的不稳定,为何法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而是认定受害者在“夸大其辞”?
空空如也
暂无小宇宙热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