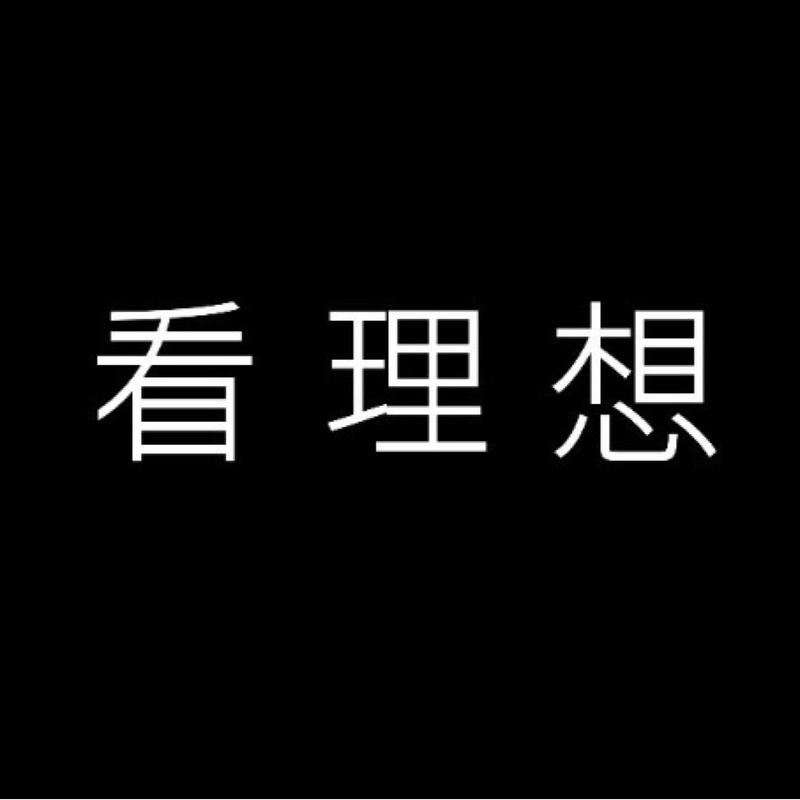时长:
22分钟
播放:
1,563
发布:
1年前
主播...
简介...
讲者介绍
成庆,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及明清禅宗史。近年来较为关注佛教现代化转型问题以及佛学通识教育与禅宗艺术的公众普及与推广。在看理想主讲《人生解忧:佛学入门40讲》。
内容提示
对我来说,在看理想工作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能够感知、触摸到真实的人。成庆老师让我最为动容的一点,就是他对学生与后辈的关爱。每每跟成老师交流,能够感受到他待人接物并非流于表面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关切,总能让大家倍感温暖。
在这个被焦虑、抑郁和倦怠情绪席卷的当今社会,作为一个佛学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成老师认为“唤醒大家的生命能量”是极其重要的事情。而他也一直在过去十余年里身体力行,尽己所能地做着实践。在本期节目里你会听到,当成庆老师还是“成庆同学”时,他在面对局限、感到迷茫时是如何做出的选择,最终又如何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志向。这些令我敬佩的老师们为什么能够做到持续稳定地输出,不知疲倦地做着“救度众生”的事情?原来,令我们敬佩的老师们,也有他们的老师。
传承就像“燃灯”,一盏油灯点燃另一盏,火光便接续不断。
从工科到财经再转向历史:成长路上的几次“脱离常轨”的选择
在关键的人生时刻,遇见了一位美国教授
林同奇先生单刀直入,以“道”相见
靠什么走出了抑郁,走出“至暗时刻”?
快问快答
精彩摘录
这些问题都是直指每个人或许最为隐秘的一段心路历程,尤其是对于重视精神生活的人而言。
如果说在我的成长经历中,哪些是让我容易感觉到压抑与限制的环境,那可能并非是物质层面,而是缺乏“意义探索”维度的思想环境。记得在读高中时,我无意当中接触到何怀宏老师写的一本小册子《生命的沉思》,介绍的是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让我特别触动,那本书我也不知道阅读了多少遍,后来进入大学后,还专门借到了帕斯卡的《思想录》,作为枕边常读的重要书籍。或许是因为对于“生命意义”的敏感,也使得我在大学阶段乃至进入职场之后,就会对周围人群的精神特质特别看重。但是作为一个工科专业背景的大学生而言,势必会面对思考与生存之间的矛盾,因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可以超越时空,无远弗届,但却常常会和当下的现实产生冲突。
从大学毕业之后的我,最初是在电信局当一名普通的电信工程师,但是我的精神却一直处于“出走”的状态,也就是对于固定职业和可预测的未来的本能性的抵抗。当我来到上海后,曾在一家不错的财经类报纸供职,但感觉自己不过是从一个粗糙的“体制牢笼”进入到一个包装更为精致的“精神鸟笼”,尽管今天看来,当时的媒体人还或多或少保持对于社会改良的理想主义热情,但是对于当时的我而言,“认知自我”仍然是更重要的诉求。因此,我再度辞职,进入华东师大攻读历史学研究生。
在华东师大的八年时间,我遇到了师大这二十年来少有的黄金岁月,人文思想风气极为活跃,除了本校诸多充满思想活力的老师,比如我的导师许纪霖老师,还有王家范老师、杨国强老师、刘擎老师等等,另外像看理想的一些主讲人,其中许多也是在师大常常遇到并且请益的老师,比如钱永祥老师、徐贲老师等等,要么就是各种公共文化活动所认识的同龄朋友,比如梁捷老师等等。可是当时对于我而言,最大的困惑其实是开始感受到学院的知识生产机制与评价机制其实并不关心“人生意义”问题,这和我当初进入学院攻读学位的初衷显然并不一致。
/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人生时刻,我遇到一位美国教授,名字叫James M. Rhodes教授,他本来是受刘擎老师邀请来给师大的硕、博士来讲一个关于沃格林的专题系列课程,而我负责一些日常的接待工作,于是和这位教授有了不少私下交流的机会,他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启发。
我还记得在第一堂课上,Rhodes教授提了一个颇让我意外的假设性问题:如果你拥有了一枚能让你拥有无上力量的魔戒,你会用它做什么?说意外,是因为在我接触的学院教育里,这一类直接针对一己的道德、灵魂的问题似乎很少遇到,更多的都是一些与生命经验脱节的概念以及宏大且抽象的理论表达,似乎那些道德议题不过是检视他人的工具而已,全然失去了对自我的审视,更将所谓的精神议题,化约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抽象理论,而不去深入探究那背后所蕴含的未知领域。
Rhode教授当时直接问我,你怎么看?记得当时的我,给出的答案其实有些模糊:我不敢确定如果真的得到这枚魔戒,我会怎么做,一方面因为内心的道德良知会阻碍我去行恶,但是同样不确定的是,那道良知的阀门能否有力量封锁内心的种种欲望?
下课后,陪他去共进晚餐,在路上,他突然略显严肃地对我说,“我对你的答案很满意。”那一刻的我,其实略微觉得有些诧异,我的答案平淡无奇,况且,这只不过是一次课堂上的头脑风暴而已,Rhodes教授的褒奖如果不是客套的话,多少也是言过其辞的。
那次课之后,每次陪他散步吃饭,我都不失时机地将心中的问题抛出,依稀记得当时的我,对于他的许多答案常有共鸣,比如Rhodes教授对于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的说法是不赞同的;更让我感到亲切的是,他的言语中不断提到“灵魂”,这个词汇几乎早就消失在我所熟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就算出现,也多是作为负面的角色。因为在现代学术看来,这样的词汇太过玄奥和主观,早已不是现代学术所探索的主题,而这恰恰是我内心里渴求探索的领域。
Rhodes教授去世之后,我读到一位曾在马凯大学读书的Lee Trepanier教授的纪念文章。在文中,他提到Rhodes教授葬礼上的来宾有很多他曾经教过的学生,职业各色各样,却没有一位在大学里任教。这足以说明,Rhodes教授在面对他的学生时,不是想着去培养一个个体制内的学者,而是单纯地将他们看作是一个追求灵魂美好的年轻人,于是尽力地去帮助他们,引导他们,甚至毫不吝惜自己的研究时间。
也正是因为Rhodes教授的启发,让我真正了解自己想要追求的“理想人生”是什么,那就是想要去探索“人为何会如此存在”,“人类的行动背后,究竟反映什么样的认知逻辑和精神底色”。
/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去了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访学,虽然我仍然对西方思想充满了兴趣,但是却隐隐感觉那并不是我能够毕生投入的领域,就在美国的访学期间,我认识了林同奇先生。
林同奇先生是著名学者林同济先生的弟弟,80年代他因为探亲之便,来到美国,后来就留在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长期担任研究员。
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那天初次会面的场景。刚走进客厅,才坐定寒暄几句,我便自然谈起此行的目的,谈起了哈佛大学著名的思想史家史华慈,以及我当时手头正在翻译的一本介绍沃格林的著作。或许是林先生觉得孺子可教,他起身走入书房,拿出那本划满红绿色标记的英文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找到一段句子,让我立刻读完,并要我谈谈想法。
这样的单刀直入令人惊讶,因为以“道”相见的情景,在我有限的学术圈阅历中不仅难遇,且与学界前辈的交往经验,多只流于人际的客套与俗情,而少有那种单纯的对于思想的渴求。
当时林先生究竟问了什么,早已忘记,但结果似乎是,林先生大概感觉这位后生的回答尚不算离谱,便提出若有闲暇,可来家中一起研读史华慈先生的这本名著。此书的中译不算精确,林先生觉得其中许多细微处在译本中并没有体现出来,甚至希望我能发心,参与到这本书的重译工作中去。当时的我,并未立即答应这个重任,一是感觉自己力有不逮,难以胜任,且有另外的翻译工作尚未完成;另则是对于先秦诸家,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道家,而对书中的儒家部分兴趣缺缺。出于自己的偏好,我只答应将庄子的章节重新尝试翻译。
从此以后,我便与林先生有了不频繁但却密集的交流。不算频繁,是因为见面次数其实不算多;说密集,则是因为每次的会面或是电话中的交流内容,都是与史华慈有关,基本没有闲话的余地。老先生有时还会主动来电,与我讨论某段文字究竟有何意涵。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心中难免有些不安,因为老先生总会问一些我根本不大会注意的细微处,例如文本中某些句子之间起承转结的语气问题。在他看来,史华慈的“秘密”就藏在这些看似简单,实则微妙的语气之中,有些貌似肯定的结论,常常会因为一个连接词而变得意思完全不同。
如此细微的文本阅读方式,事后想来,应该是林先生非常尊敬与重视史华慈的思想,才会以对待经典的方式阅读其文本;另一方面,则是林先生的阅读研究习惯就是如此。无论是他翻译《在中国发现历史》,还是他对牟宗三《圆善论》的解读,都可以看到林先生的这种文本解读风格的特点,细密而有见解,同时也有思想的大局观,使得看上去琐碎的解读,最后仍能归于某些宏大的思想关切。而对于林先生治学的这些体会,我当时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而是很久之后才慢慢体悟出来的。
林同奇先生关心的,其实是古来至今各个核心文明所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人”是怎样的存在?虽然他并没有时间来系统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多是借着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来寻找他心目中的答案。但从某个意义上而言,他对牟宗三、史华慈的关注,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点燃了他早年的关怀,从此开启了一段新的思想旅程。
对于当时正处于“精神迷途”的我,能够与林先生相遇、向他请益,学问上的收获自然是无疑的,但是更令我感觉共鸣的是,他在日趋僵化的学院生活中给我展现了一位纯粹的“寻道者”的生命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和Rhodes教授都是在以他们的治学、思考为我未来的学院生活指引了某种可能的方向。虽然他们治学的领域和我如今关注的学术领域没有太多关系,他们当初在学术上的指导也似乎只留存了一些吉光片羽,但是他们给我传递出的讯息是,这种精神的寻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其特别的价值与意义。
现在回想起来,老人的生活是简朴而规律的,坐拥一块小池塘的阳台大概是他休息、放松的地方,一旦坐在那里,老人谈论的内容似乎才可以暂时远离史华慈。在那里,他会兴致勃勃地为我介绍为鸟儿喂食的投食器,也会问问我未来的学术计划等等,林先生也热心地给我提了许多建议,但这些建议,往往最终又不知不觉地绕回到对史华慈观点的讨论上。
/
离开波士顿后,我开始投入到汉传佛教的学习和实践中去,之所以转到佛学领域,也是和自己当时低迷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想要寻找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于是接触到佛教的禅修,学习上座部佛教和汉传佛教的一些修行方法,这也让我非常迅速地感受到效果,这不仅开启了我对人类精神活动认知的另外一个角度,而且作为修行实践的副产品,也解决了我持续很长时间的心理抑郁问题,这也让我对这种东方的心理治疗方法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与信心,确切地说,它激发起我非常强烈的好奇心。
佛教面对精神体验的方式,一方面是让你通过禅修的方式安定身心,然后利用这样的身心安定状态去观察我们是如何认知自己的身心以及外界的环境。因此,禅修其实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方法,只是利用我们自己的“心”来作认知的实验,当然,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正是这一次短暂而有效的禅修体验,我慢慢越发深入地去接触佛教理论与修行的想法。因为这种理论与实践兼具的特质非常符合我对精神探索的理解,虽然艺术的审美体验依然吸引著我,但是那种审美体验难以预期,更像是一场长途跋涉中的偶遇而已。从那之后,我开始密集地学习佛学理论与相关的修行方法。所以我认为,坐禅的体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启发,因为它让我直接切入到佛教谈的所谓“心性”的核心领域。
对我而言,艺术的审美体验与禅修的体验是非常难得的人生经验,这种经验的获得固然与我自己的寻求努力有关,但是同时也蕴含了许多我尚无法理解的深层原因。正是这些体验,让我开始反思过去的那种以纯粹的理性知识为路径的学习方向,更让我对现代学术体系下的知识分科方式产生深深地质疑。因为我模糊地感觉到,那种探索方式与路径并不足以让我获得的关于世界的答案。
/
现在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学习经历,之所以能够遇到这么多位能在不同层面上给予我启发的良师益友,某方面当然可以归结于某些看不见的因缘,但或许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一直没有失去探索生命意义的初心,虽然这个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所谓的“至暗时刻”,但今天看来,那不过是精神探索的题中之义,因为正是有困惑,有痛苦,我们才会去探索,才会去寻找。这让我想起大学时读帕斯卡的《思想录》时最感动的一句话:
“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
评价...
空空如也
小宇宙热门评论...

风声潇潇
1年前
广东
7
非常喜欢成庆老师分享的内容,当代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老师。谢谢

多茶E
1年前
福建
3
听成庆老师的声音,内心很安定。

冯嘻嘻_ZfC0
1年前
广西
3
太喜欢成老师了

怪石樗木
1年前
浙江
2
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寻着的人。

鲸鱼LJY
9个月前
河北
2
我光在原地哭了 希望有力量往前看

夏桐Tiao
1年前
陕西
1
我就是那种一边哭一边爬的人

cici223
1年前
北京
0
来学习

鱼游水
1年前
上海
0
不断的精神追求

YF01
1年前
广东
0
20:26 妈妈叨叨叨没完没了~这时候,正念地听是一个应对的好方法😄

betterTetter
9个月前
上海
0
“我要同等地既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