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分
暂无评分
0人评价
5星
0%
4星
0%
3星
0%
2星
0%
1星
0%
AI智能总结...
AI 正在思考中...
本集内容尚未生成 AI 总结
简介...
本期节目我们阅读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破晓时分》,作者是台湾杰出小说家朱西甯。
朱西甯的创作生涯超过半个世纪,留下了30多本文学作品。
张爱玲说他“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莫言则把他看作自己“真正的先驱”,唐诺认为,纯粹从文学的角度讲,朱西甯是 1949 年至今台湾最优秀的小说家,如果加上“之一”的话,大概也没有几个。
除了他自身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外,朱氏一家也在台湾文坛有不可替换的独特地位。
你会听到:
1、朱西甯是谁?为什么说他是台湾最优秀的小说家?
2、关于“有事”的小说和“没事”的小说。
3、分享书中最喜欢的篇目和段落。
相关作品:
老舍作品
主播:大壹 / 超哥 / 星光
主播...

杨大壹

文化有限的超哥

星光
评价...
空空如也
小宇宙热门评论...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4年前
65
去年回家,我到西门小街那家早点铺,是我初中同学家的店,一进门,撞见他正在炒杂酱,耳朵侧别着一支云烟,皮肤黝黑,原来,店主已经换成了他。我本想扭头换一家,却和他眼对眼碰上了,无奈,只好坐下。
点了一碗豆花米线,他麻利地抓起一把米线,一边烫,一边往碗里舀佐料,特意给我两大勺豆花,眼看快要做好,我起身去端,他一看,说:“你坐下坐下,我会端过去。”
我在等待期间看到,客人点的餐都是他端到桌子上,他和另一个人操持着整个店。但我不能接受他把碗端到我面前,我不能接受自己变成他服务的对象,可再怎么不能接受,我已经被服务了,这种被服务,让我莫名有了一种耻感,一种愧疚——如果不是我足够幸运,我和他如今的境遇应该是相似的。
我坐在板凳上,他坐在我对面,我不好意思动筷子,他问:"你现在是在哪点?”我说:“在北京。”他很惊讶:“嚯,当时班上你学习就最好,还是你有本事。是做什么工作?”我满脸通红,不知道要如何跟他解释我的工作,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多么小心翼翼地措辞解释,都会对他形成一种压力,我只能打哈哈:“替别人打工,混口饭,你看我这头发,都要掉光了。”他听了直笑:“那你先吃,要什么再点,我去忙。”
看他起身,我松了口气。我低着头,一边往嘴里划米线,一边质问自己:“你想念的故乡,有包括他吗?为什么没有?是忘了吗?。”
故乡仿佛是一块长在我脸上的胎记,我想把胎记抹去,可一旦彻底抹去,我便无法证明我到底是谁,如果留它在脸上,又让我自卑得想找个洞钻进去,在抹去和不抹去之间,我挣扎,撕扯。
更深的撕扯,是我逛菜市场的时候。那个菜市场,在我出生前就存在,回家后,每天上午跑完步,我都会去菜市场拍照,我举着镜头,对准腌菜摊的摊主和她背上熟睡的孩子,对准戴着头巾卖瓜的满脸笑容的奶奶,对准抽水烟筒的爷爷,对准我熟悉又陌生的一切,我把一切都当作一种风光,一种被称为“烟火气”的风光。
我在菜市场,看到一位大爷挑着扁担吆喝:“土蜂蜜,土蜂蜜,要的么来啦,要的么来啦。”我被吆喝声吸引,我想和他攀谈几句,想身体力行找回城市里所没有的温情,于是我叫住他:“蜂蜜咋个卖?”
我并不想买,我只想看看,想和他说几句话,他一听,立刻把扁担放下:“我这个蜂蜜么最好啦,你克别处都找不着。”一边说,一边打开罐子,蜂蜜的甜香扑鼻而来,几只死去的蜜蜂粘在表面,如琥珀一样。
我继续寒暄:“确实好,但我没有带瓶子。”我本想以这句话结尾,不愿再耽误他,不曾想,他迅速掏出一个塑料瓶,问:“你要多少?一瓶给够了?”我连忙说:“不用不用,好确实好,但我钱没带够,不好意思,下次,赶下次。”
我分明看到他收起瓶子时失落的眼神,那双眼睛很浊,皱纹密布,像蜂巢的纹路。他费力地从地上重新挑起扁担,我意识到,我做了错事......
后来,我遇到不少人,把那些无法逃离故乡的人视为没有能力没有想法,活该被淘汰活该受苦受穷的人,可他们不是没有能力没有想法,他们是被框定在那样的境遇中,无法逃离。
结构性的枷锁会锁住他们想象其他可能的可能性——我们镇上的孩子,大多都认为,以后在镇上打工,养活自己就可以了,他们之所以这么想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向外探求的渴望,而是向外探求的路上早已竖满了层层屏障,这些屏障将社会分层不同阶级,每一个阶级的人可以想象的自己能获得的高度和能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通过网络,通过媒体,他们当然知道有另外一个世界,但因为那个世界太过遥不可及,所以显得与他们无关,所以即便他们知道自己无法拥有被其他阶级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他们也不会有被剥夺和被排斥的感受。
记得刚到北京的时候,第一次去国家博物馆,看到很多小孩子穿着整齐的校服,在一个个展区听老师讲解,有老师让孩子们回家模仿活字印刷,刻自己的名字,有老师在远古人展区给孩子讲分子人类学,回去以后我和我妈说起,我妈说,镇里二小有个三年级的学生在田里被拖拉机压断了腿......
那些无形的屏障,不单单是“贫穷”可以概括。
逃离故乡后,每次回家,我都为我的幸运感到愧疚,在贪婪汲取熟悉的食物和风景时,我又为我变成了故乡的游客而愧疚,愧疚却又窃喜,窃喜之后又是愧疚……

黎霹雳
4年前
60
配乐好听

星光
4年前
41
【福利】感谢理想国提供的朱西甯纸质书2本套装(含《破晓时分》《狼》),欢迎你在留言区说说:你对家乡的感情,或者是对乡愁的理解。
我们会选出5位朋友送出套装书,截止时间2021年6月20日24:00,期待你的留言!

去捞星辰大海吧
4年前
37
我对家乡的感情,高中之前一直想要逃离,上大学的时候就觉得只要不在家随便去哪都行,毕业之后也并不想留在家里工作,直到工作几年后,突然回家走街串巷的时候,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仿佛自己能闭着眼睛就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安全感油然而生。对家乡的想念,大部分来自于对亲人的思念,哈哈,突然庆幸自己虽然不在家工作,但是是和家乡的人结婚的,我们从初中相识,彼此熟悉相爱,逢年过节一起回家,也蛮好的。

我不跑调
4年前
34
推荐有机会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赖声川和王伟忠合作推出的《宝岛一村》,讲述的是49到60年代一个眷村的故事。从大陆到台湾的人们组成了四个家庭。没有特别跌宕的情节,就像朱老师说的那种“没事”。选秀没有一炮而红,私奔没有成功。但最后,他们终于等到了能够回到大陆故乡的那天,找到了熟悉的乡音、亲人,和陌生的坟墓。欢笑和泪水在空气里揉成一团,是特别好的特别真诚的故事。

尖沙咀
4年前
20
唯独这一期。我有特别多发自内心的故事可以讲。关于家乡,关于乡愁。往狭窄的议题里退缩,不得不谈到原生家庭,和出生的城市。狭窄而又模糊,抽象而又具体,我一辈子都不想回去,我更不会怀念。
我出生在一个最糟糕的家庭,和一个文化荒漠的城市。艺考来的北京,现在在北京有五六七八年了吧。老家在秦皇岛(你们也许觉得阿那亚很有名,但那是唯一的绿洲,而且是个地产项目,活跃的也是北京中产,和这城市貌似没啥关系)北京的隔壁。虽然高铁俩小时,到这绝对是我脑神经打开和闭合的状态。直到2015艺考来到北京,我才拔回了我被偷走的时间,以及紧闭的眼睛。
对比大家对于家长的回忆,我小时候并没有无忧无虑的场景和生活状态。爸妈离婚又各自再婚,奶奶原始积累给爸爸的房子,她为了和服务员小三在一起,作为离婚财产给了妈妈,而妈妈把这房子出租后又把它作为和继父生活的住所,他们又各自生子。我的童年就在这两栋烂尾楼间展开,初中没人接没人送,在校园凌霸和家庭凌霸间用那百分之一的力气,撕裂的喘息着。初中一个女生带头孤立我,不允许我嬉笑打闹不允许我学习我允许我说话,夺走我所有的表情,我和妈妈说,妈妈说“你活该”。以至于我在考前那段仍旧有嗜睡症、人格障碍。就这样,小升初可以做出数学卷附加题的我,莫名其妙被分到了最差的初中,进了一所垃圾高中。那是难以言说的混乱。至今觉得校园凌霸该坐牢。在人格养成和成长的阶段,我所经历的都是窒息的反向操作。连初夏傍晚的空气,都伴随着恐惧。整个生命的出口就是画画了。因为手握着笔,就可以产粮。篇幅有限,关于之前的十几年,那些模糊的记忆,懒得回忆也懒得描述了,因为这个城市太无聊了,它让你看不到一丝生机。
直到高三看到北京某艺考机构的广告,一张火车票送到北京。几年以前刚下高铁的感觉是,哇 世界真大 世界原来是这样。在机构生活学习了一个星期,就完全忘掉了我从哪来的,之前那些面目可憎的人也都变成了模糊的面孔。我的耳边是讲着康定斯基的老师,说他是数理化与音乐共振的抽象派画家,机构的founder在讲着他的传奇故事,浑身都是沸腾的热血,我看到了文明的世界是怎样运转的,收获了五湖四海的朋友,不同的性格,也带着各自不同城市的性格与印记,在那个无知的年纪里,至少告诉我,世界是这样的丰富。艺考总是一个概率游戏。考试前一晚因为没有父母陪同,在燕郊 被偷了手机的我带着恐惧 一晚未睡,因此也有了复1复2,在复读的过程中,也认识了为了Dream school复读了10年的主教老师,她说如果她重来,大概还是一条汉子。老师会因为半夜来了灵感,而在凌晨范画。而我也时常在凌晨能更好的产粮。这也只有在北京,我们能够习以为常。无数次彻夜的狂欢,高歌,大家一起等明天,然后再接近明天的时候,累了,不人不鬼的走散了,好像每一次酩酊大醉也好 爬上天台高歌也好 过场都是一样的。美好而乏味。在复读的日子里,长大了那么一两岁。却明显累了,我去到了人更多竞争更激烈的机构,也见识到了人是如何每天都在斗争中前进。一直在给灰色产业创收,艺考机构大多是触碰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吧。各种班型,各种收费,协议班、保过班、老师和学生乱搞,喜欢谁就给谁一直改画。但也是在这样的强竞争中,人得已飞速成长,迅速的接收信息。见证了身边的人来来走走,奔向不同的高地,我们不再是我们。离得近的离得远的,近到同坐14号线,居然总能碰到。虽然想出去闯荡的热枕没有褪去过,但却发现江湖不是想象的那样。但我们仍然期待着,有趣的瓜,丰富的故事,711的速食柜台,以及这城市迷人的夜色。打这些字的时候我正在三里屯打车,前边拍了50多号还没到我哈哈哈哈
把青春献给身后的这座城市,为了这个城市我们付出这代价。哪怕是无限loop,但我在北京可以接近这些最敏感的神经,会遇到相似的人,可以deep。讲出来不会被嘲笑,相信正念。可能大家会有家乡情结,根植在心灵最深处,可能是累了的时候,可能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但我却从始至终,都对我的老家没有一丝丝想念。正因为离开,我才在朋友身上获得爱,我才去到了不同的城市,触摸到了光。才得到正念看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一辈子都要远离的。个人情感是处于一种陡峻的平衡中的,我中间每一次回去,都觉得 我永远不会属于这里。尖锐锋利是因为时间流转,它给了我那么多深刻和重复,但我每次回去都如此抽离,认清了到你接纳不了。有些胆怯惶恐也是合乎情理的。
故乡你好,故乡再见。

杨大壹
4年前
18
1:05:55 补一个可能的彩蛋,1949年是牛年,所以小朋友叫犇犇

温温
4年前
17
🙋要推荐一下台湾的原住民歌手胡德夫先生,他在20世纪70年代和朋友一起推动了被称为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启蒙运动的“民歌运动”,很多音乐作品都和当时的历史政治事件有关联。尤其喜欢《太平洋的风》、《匆匆》、《美丽岛》,音乐里能听到山川、河流、海洋、乡愁、眷恋、对人生的思考和热爱。

AGAAR
4年前
15
感觉超哥 大壹 星光三个人分析问题的角度像某个人的三个面 也像三个不同的人 整合出来就特全面的感觉 超哥代表了生活的油盐酱醋茶的面 平和温暖 大壹代表了脱离世俗的理性层面很冷静温和 星光就是一个年轻人的观点有叛逆也有思考 热烈激进

火炎焱_LGMr
4年前
13
我是一个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小孩,对于没有离开过家乡的人很难有多深刻的印象。说一下我外婆的故事吧,她生于1935年的山东临沂,两年后日本人全面侵华,8岁那年她随家人逃难到上海,离开时她坐着马车,看着身后高大的城墙渐行渐远,看着城墙旁的石狮子慢慢消失。尔后在上海落地生根,五十多年后我母亲陪着她重返故土,高大的城墙没有了,城门旁的石狮子没有了,那个小时候玩耍过的几进几出的大宅院没有了,外公外婆也没有。那个年代,一声再见可能就是永别!

我和你说当初
4年前
8
早

七个梦
4年前
8
01:14:12分享罗大佑的专辑《之乎者也》: http://music.163.com/album/10855/

七个梦
4年前
8
04:01朱家朱星光🙊

morningstarchen
4年前
8
习惯了互联网快餐工具书阅读,刚开始看这本书时是不适应的,里面的每一个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心思,要慢慢读,不能一带而过。说到乡愁,文中用到了“刺闹”一词,把我瞬间带回了家,回到爷爷奶奶身边,还忍不住学着他们的口音念了出来,哈哈,一词还乡~

白色森林
4年前
8
这一周的工作真的是从听文化有限开始的,听了一整个通勤路,再去买杯冰咖啡,今天一定会元气满满的

我不跑调
4年前
8
16:44 “有事的小说好写,没事的小说不好写。”🤔有一点哲学在里面

款款野屮_
4年前
7
可能是还没有扎根于另一个城市,只是一个北方女孩在南方读书,其实自己对家乡的感触远远没有那么深刻。第一次被“家乡”这个概念触动到是在高考之后和爷爷一起翻旧相册,听爷爷讲他从前的故事,那些关于家,关于求学,关于假日海边的少年。爷爷年轻时随着家里到北京读书,随后又到广州工作,小时候一直疑问为什么最终父亲和我还是出生在这个北方小城。那天我也问出我问过很多次的这个问题,答案还是相同,爷爷笑着,“因为家在这里呀”。相册里那些其他城市热烈的故事,最终都抵不过一张与家乡童年玩伴的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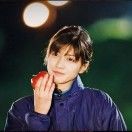
confidential
4年前
7
13:19他让我不要学外在世界枯萎,不得不凝视内在微观自我的,所谓新生代作家,而保持广阔的宏观视野。

下雨天吃巧克力
4年前
6
最近在恶补之前没听的节目,非常舒爽。太喜欢听你们讲书、聊书了,已经被种草了很多想读的书。在不能听节目的时候,就去即刻看你们的动态😍太爱你们了😘😘跟你们一起成长!

小魔法师
4年前
5
家在一个小村子里,民风特别纯朴,邻里关系特别融洽。下午去江边跑步,每跑一小会儿,就有一个老熟人迎面走来,不忘唠嗑几句:“妹妹今天又来跑步啦”“别跑太久啦”“跑完早点回家吃饭”……经常有邻居包了饺子也给我们送一份尝尝鲜,妈妈也经常拿水果到邻居家分着吃,感觉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爱意的包围下成长的。身边的一些朋友说我很会照顾人、关心人,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的家乡和家乡的人们赋予我、教会我的。
渐渐长大,我开始期待更加广阔的天地,所以初高中、大学都选在了离家很远的城市。大城市确实比小乡村有很多的机遇、更多奇妙的体验:参加绘图比赛;和朋友沿着珠江夜骑,扛着车过天桥、穿过火车轨道;参加了读者分享会,听大家分享自己的观点……还有很多数不胜数的美好瞬间。但是也要承担更多的压力,就不细说啦,可能当下我觉得做起来很辛苦很费劲的事情,事后再想想就会觉得:其实也就那样吧~move on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想想我住的小村庄,心情会得到极大的放松~ 感觉我只有我熟悉的事物才能让我放松下来。前两年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回家乡支教。我的家乡让我成长为一个不算太差的人,我还蛮希望我能尽自己所能也为我的家乡发一点光吧。现在正在认真地写教案啦,希望能陪伴家乡的孩子们度过一个特别的暑假。(前阵子重新听了“他乡的童年”那期节目,对我的课程设计有好大的启发呢!感谢文化有限!感谢超哥,大壹老师和星光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