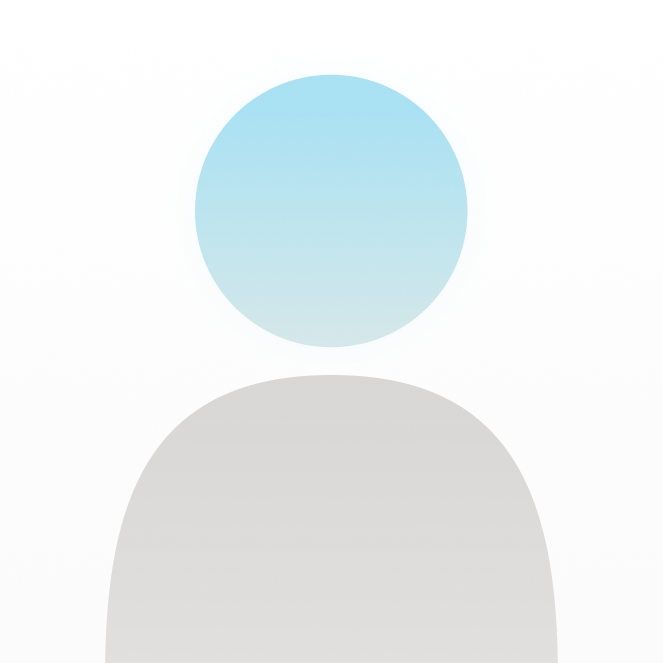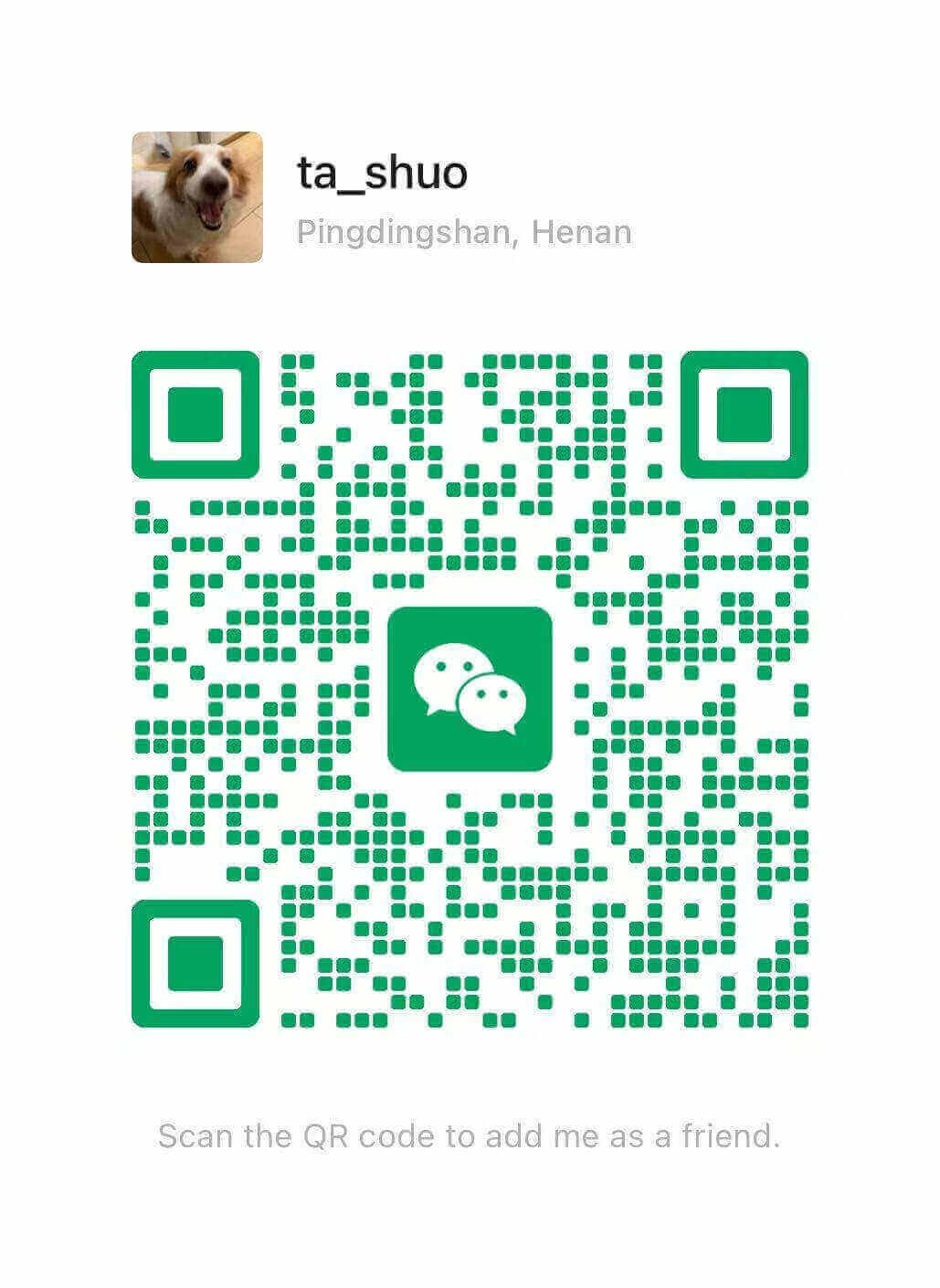这是游牧教室「人文阅读课」的最新一期,文档请点这里
出场:我、八年级的陆同学
[意外发现,这一次所讲的内容,正是浙江省2021年6月高考历史卷大题。陆同学,去高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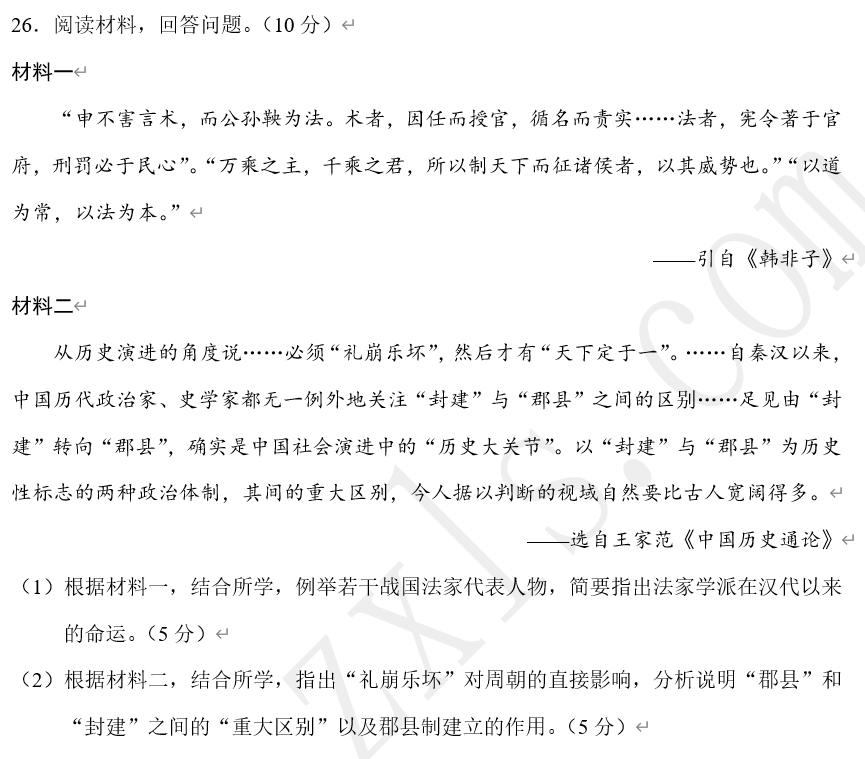
(选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汉承秦制。自汉而后两千年,国家控制方略时有变易,由秦开创的大一统体制则一脉相承,分久则必合。然追究秦制,由涓涓之流汇成江河,实为春秋战国社会变迁的集大成者,其变亦由来已久。其变由来亦久矣。
秦亡后六年出生的贾谊,在检讨秦兴亡的名篇《过秦论》里就说过,秦统一六国的功业,乃是“奋六世之余烈”,非始于始皇一代。
相比起贾谊,顾炎武要追溯得更远些。他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时则绝不言(周)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一无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顾炎武是从社会风气看变迁,着眼于春秋以来“封建”礼仪的丧失。133年,他是从《春秋》终篇算到六国称王之年。“六国称王”,在旧史家看来,确实是乾坤倒转的“大世变”。上面两位古贤说得都不完全。商周“封建”体制转变为秦“大一统”体制,虽然不能与“传统”体制转变为“现代”体制相提并论,但在一点上却有相似处,即两者都不是局部的、一事一项的变迁,而是由一系列相关性变迁运动构成的一种大变局。这不只关系着治道、政术、教化,更关系到政体,亦即国家根本体制的大变局。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范畴内,最为深刻的一次具时代转折意义的变迁。
这种变迁的特有情味,可以通过下面的事实得到应验:“百家争鸣”这样的思想开放,只有这一次;战国至秦这样上中下“涡流式”的社会变动,也仅此一次。它们在以后长达两千年的时段内再也不曾重现过,直到近代社会变迁开始。
今日我们若更为宏观地来看,西周“封建”的蜕变,一开始就植根于体制内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二元对峙,彼长此消,演变到春秋时代已经不成模样。秦的“大一统”体制,正如“百川异源,皆归于海”,它是会聚八百年的小变、渐变而终成大变局。凡是历史上的大变局也莫不如此。
对这次变迁的情节,各种“通史”都给予高度关注(变迁的性质又当别论,现在多数仍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定性),重要环节都不会有大的遗漏,至多详略不一。除前数次提到的吕思勉专著外,新出的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从官吏制度、郡县制度、封君制度、俸禄制度、上计制度、户籍制度、财政赋税制度、爵秩等级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十多个方面,备述了战国时期变迁的细节。白寿彝新编12卷本《中国通史》,前后甚至一卷之内观点都不尽一致,这是“大集体”编写难免的通病,但从综合晚近各种研究成果的角度来看,颇可参阅。另外,比较忽略海外华人学者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也是该书的一个缺憾。
总而言之,以周王“共主”地位丧失、“联邦”体制解体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变迁,是诸多因素的合力促成的,其中长期的兼并战争与各诸侯邦国内部的各种权力斗争,都起着助燃爆破的作用。其重要关节大致有三:
一是列国的区域开发和地缘政治的拓展。
在讲述这一问题之前,先得说一下有关区域发展与统一的关系。
与旧史观不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中国的历史发展同样是多元的综合。中国历史不支持“一元起源论”。考古发现逐渐显示,中国文明的起源绝非纯粹是由中原向四处辐射的结果,相反四周也不断地为中原的发展提供活力(魏晋南北朝那一次最为典型),两者反复互动,取长补短。因此,“统一”是一种长期的历史运动,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各区域自身的发展。
商、周在由各区域发展整合为“一统天下”的历史长途中,无疑是重要的两站。但还是应实事求是地估定它们所涉的地域,用“统一”的长镜头给它们准确的定位。
首先,商周王国的自领区域跟与其联盟的区域不是一回事,后者实际是地方自治的。再进一步说,即使就联盟所涉的区域而言,也有一定的范围,不能随意放大。据现有的考古,商人曾到达过的地方,其东境最远也只到今潍坊以西,西周才扩展到整个山东半岛。从《中国文物报》获悉,轰动一时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经长达九年的整理研究,终于以《新干商代大墓》专著形式面世。著者认为“大量实物资料证明,商代赣鄱地区有一个大的政治集团,这里的文化发展至少与中原相当,是一支与中原商文化并行发展的南土方国文化”。我觉得,这一结论比之“统一论者”更接近历史实际。著者没有明说,在我理解所谓“并行”,就是它尚未进入商联邦的视界。南方究竟最远到达哪里,是不是跨过了长江,还需继续寻找充分的实证,但四川与长江中游的巴蜀,西周时尚未到达,到了秦统一战争后才进入秦版图,这是显而易见的。相反,东北辽河流域以及中原北境,却一直是商周及商周以前古部族交叉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它们很早就与中原部族的活动联结在一起。但这里的分合无定的状态也最严重,一直延续到秦汉以后。
回到西周“封建”各诸侯国,它们实际是包含着宗族血缘与区域地缘二元因素的混合体。各诸侯国之内,都有不同部族的土著方邦居住;三晋地区,更是长期与狄戎诸族交错杂处。那时究竟有多少部族邦国,很难弄得清楚。《荀子·儒效》说西周“兼制天下”共71国,这是指大的邦国;而《吕氏春秋·观世》则说有“封国”400多,“服国”800多。吕思勉先生在好多地方都说,准确的数字恐怕已不可而得了。
从西周建国到秦统一,历时八百余年之久。当初封建的诸国经长期经营,农业发展、人口增殖都很快,二三百年后已非昔日面貌,更不用说入战国后。西周以亲缘化解、融合地缘的政策非常成功——“同姓不婚”的族外婚制成了特异的黏合剂。在每个以大国为中心的区域内,接触—冲突—交流—融合—整合的过程走了一圈又一圈,到战国时期,以大国为核心,若干区域地缘政治的特色已十分明显。春秋时代大约有一二百个邦国,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见于文献的只有十余国,大国仅七。不说大国,就以鲁国为例,为其兼并而为附庸的,史载即有项、须句、邿、鄟、鄫、卞等小邦邑,它们都已经整合进了统一的鲁文化圈。
从春秋战国倒过去,反看清楚一个问题:不管西周建立初有多少邦国,邦国之内、邦国之间都存在有不小的空隙地带。那时的人地比差很大,人少地多。由国君直接管辖的郡、县,其中不少便首先是在邦国内空隙地带或邦国与邦国之间交界的空隙地带设置的。这就是区域人口和地缘经济发展的标志。郡县与原来的封邑不同,官员都由国君直接任命而不世袭。“大一统”就是这种地方行政系统“制度创新”的推广和全面实施。但对于大中国的统一来说,历春秋战国550年,巴蜀对四川地区的统一、楚国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统一、吴越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统一,三者意义最大。如此到秦统一,“中国”不仅已入川,且越过长江而进至珠江流域。但也应该说清楚,秦对后两个区域的整合程度远不能与中原、河淮地区相比——“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岂偶然哉?
总之,秦的大一统建筑在诸国各自区域统一的基础之上,是没有疑问的。
空空如也
暂无小宇宙热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