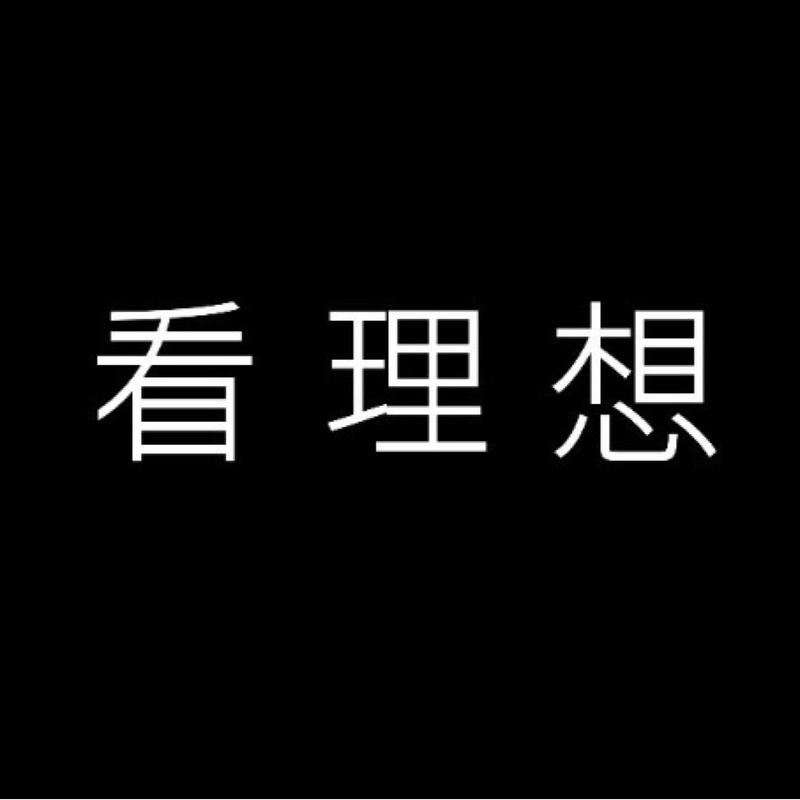时长:
86分钟
播放:
6,365
发布:
7个月前
主播...
简介...
2024年,是恶性事件高发的一年。珠海驾车撞人、宜兴校园行凶…在多起无差别行凶案件发生后,我们可能在心里问了无数次:为什么?
当我们切身感觉“我们与恶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近了,却没有人告诉我们,究竟这恶从何而来,我们又还能怎么办。
本期“看理想时刻”,我们请看理想《致独特的你:人格心理学40讲》主讲人王芳老师,从心理学角度和我们谈谈如何面对“我们与恶的距离”。
*点击时间码,可直接跳转至王芳老师答问部分
05:26 《我们与恶的距离》,今天为什么仍然让我们回味?
07:31 为什么剧中最后没有告诉我们李晓明行凶的原因?
11:57 分析恶性行凶者的成因,会有“洗地”的嫌疑吗?
17:36 什么是“恶的他者化”?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恶人”?
22:57 男性更容易犯下恶性事件吗?这和“有毒的男子气概”有什么关联吗?
28:24 为什么有人会把刀挥向“无冤无仇的人”?特别是“更弱者”?是想“报复社会”,还是“找存在感”?
对某个群体的仇恨被合理化,是恶性事件更可怕的后果?
32:14 恶性事件罪犯的心理成因有多复杂?什么是日常生活的“危机点”?
41:40 同样经历创伤,为什么有的人会变得更善良,有的人会更相信“丛林法则”?
43:28 精神上的问题和犯罪行为有关联吗?如何理解暗黑人格、反社会人格?
48:20 我们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精神问题?诊断病理,还缺少什么学科的视角?
53:15 在心理危机干预、社会支持系统上,个人和社会还能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修建自己的“安全系统”吗?个人关系世界、社会关系世界存在互相补偿的机制吗?
1:04:03 心理学最近几年渐成显学,为什么让人不安?
1:10:16 NPD、PUA、PTSD…心理学概念的日常化,会助长人们之间的对立吗?普通人如何运用心理学更好地帮助我们?
1:18:45 闲聊开始:平时怎么放松,韩综《思想验证区域》观感…
最后,借用王芳老师的祝福,愿你的身边有光,愿你就是那道光。
本期推荐
王芳 主讲《致独特的你:人格心理学40讲》
本期嘉宾 | 王芳,北师大心理学部教授,看理想主讲人
本期采访、制作 | dy
本期摘录
《我们与恶的距离》每一集最开始那个社会事件,它把更广泛意义上有可能作恶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纳进来了,然后它会去展示可能每一个面向经历的那些创痛也好,挣扎也好,那种人性的摇摆,很细细细密密的展示出来,进而可能就会让你意识到说,原来所谓的罪恶,还有罪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那个人性都是如此的复杂。
/
当一个杀人案发生,你不仅要去关注杀人案本身,更要关注对于方方面面的伤害。于是也就更要回过头去追问——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而不只是说,快点判死刑杀掉就好。以及对于大众来说,如果这已经是一个社会事件了,那么大众是有知情权的。
知道并不等于理解,理解也不等于认同,更不等于支持。如果说了解了成因,就会为犯罪开脱,这太没逻辑了,同时也太看轻——多数人是有基本的道德判断的,以及司法的独立性。
/
所谓“恶的他者化”,也就是说我们会习惯性的把邪恶想象成完全有别于自己的,甚至非同寻常的,很罕见又难以理解的存在。而它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可能会因此而忽略,或者没有办法辨识出,那些其实是在频繁制造邪恶的、也许非常稀松平常的一些环境性的特征。
另外,“恶的他者化”还可能带来一个反向的作用,就是我们把他者视为是邪恶的,并且就只在他者身上看见我们所害怕的东西,那么到头来,所有被我们认作是他者的东西,所有陌生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邪恶的,它就循环上了。
换言之,我们刻意去拉远自己和恶的距离,恶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我们就有可能在未来完全被动的、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猝不及防就会撞上这个恶的随机发生。
反过来,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与恶的距离没有那么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就是一线之隔、触手可及的,那反而就会让我们时刻对潜在的恶是保持警惕的,进而也有可能去做预判和防范。
/
父权制所设定的一整套游戏规则,对男性这个层面的压迫,就是作为一个男性,你需要在一个代表权力和地位的梯子上不断向上攀爬,这样你才是有价值的。但是往上爬也就意味着可能随时失足跌落。于是就要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去维护,或是再去向上争取地位。
比如争名夺利就是一种方式,积攒财富是一种方式,征服女性是一种方式,暴力也是。
暴力也不只有直接的攻击,比如像通过暴力引发了别人对自己的关注,也是一种“地位提升”。
如果我们去看这些人的经历,他们多半都有过社会受挫的经验,而那个挫败的主题,通常都会跟文化当中常见的一些男性主题是有关的,比如说野心、金钱、求偶之类的,而受挫就意味着地位的跌落和失权,意味着自我价值的一种贬低和否定。
那这个时候,“暴力”这种跟男性气质深度捆绑的行为,就会成为一种用以恢复地位、获取自尊,然后同时展示自己所谓“男性气概”的一个方式。
/
那些被伤害的人,从个体层面上来看,好像的确和行凶者无冤无仇,但如果受害者是行凶者所仇恨的“外群体”的一员,比如你是让我遭遇不公对待的那个群体当中的一份子,哪怕这个连接非常牵强,比如说你是那个让我不爽的这个学校里的人,你们其他所有人都是迫害我的当中的一部分,那他的攻击伤害行为也是可以被合理化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行凶者的主观感受上,他认为他伤害的对象并不是完全的“无冤无仇”。
其实这种大规模的行凶或者是暴力的犯罪者,他们往往并不是一时冲动,是有谋划的。他们其实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这些行为是不被法律和道德所允许的,所以他们要给自己找理由,要想办法去解释、甚至美化自己的恶行。而这一部分反而有的时候是会被某些人买单的。
特别是对于外群体的仇恨,当它本身就代表着某种社会情绪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人会为这种极端的暴力拍手叫好,这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部分。
/
国外有一个研究项目,很难得去梳理了这种所谓大规模的攻击者的一些能找到的材料,结果就发现其中有42%的杀手在童年的时候是经历过创伤的,多数是身体暴力或者性虐待,或者目睹过父母自杀,或者是遭遇过严重的校园欺凌;有超过80%的人,大概在事件发生前的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里是达到了一个所谓的危机点,比如说被停职、被解雇,亲密关系破裂,被社会排斥或者陷入个人经济危机等等。
这些危机会引发他们在后续行为上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强烈的焦虑,孤立,然后绝望。他们会感到自己被抛弃了,被羞辱了,被边缘化了,甚至产生自我厌恶。但是这种自我厌恶,最后都外化成了都是别人的错。进而会心怀不满,然后充满了愤怒,紧接着就会开始去策划这种大规模的杀戮。
/
大多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并不暴力,他们甚至更有可能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而不是肇事者。这里我也看过一个数据,说如果一个人患有精神分裂症,那他杀死一个陌生人的可能性只有14.4万分之一。但是我们会看到,好像每当有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听到凶手就是个疯子,肯定有精神病。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说法确实提供了我们对于一件非常出乎意料、不合逻辑、难以理解的事情,这其实是经常陷入一个循环论证——我们先问,这个人为什么做这么可怕的事情,因为他有精神病,那你怎么知道他有精神病呢?因为他做了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
/
有一个理论就讲到,一个人的社会安全系统其实是由两个世界构成的,一个就是个人关系世界,包括比如像我们的伴侣、家人、朋友、关系很好的同事等等,他们可以提供给我们情感连接,以及重要的社会支持。另一个呢,就是社会关系世界,像我们所在的公司,单位,学校,社区,再广大一点,各种社会机构,社会制度乃至整体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稳定程度等等,他们提供给我们经济来源、社会身份、社会保障、社会秩序以及像公平正义这种抽象的道德和价值的依托。
这两个世界其实是有一个相互代偿的关系的,就是任何一个系统失灵,人们就会转而去向另一个去获取必要的安全感。
如果一个人同时对两方面的信任都断裂了,那就很可能会进入一种极度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当中,进而寻求一个极端报复,同时也是在寻求自我毁灭。
/
互助就是最小的系统,我们有时候把“系统”想得太大了,有时两个人之间的那些相互的善意的释放,它就是改变我们两个人实实在在的所处的那个环境和情境的一种方式。
当我们切身感觉“我们与恶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近了,却没有人告诉我们,究竟这恶从何而来,我们又还能怎么办。
本期“看理想时刻”,我们请看理想《致独特的你:人格心理学40讲》主讲人王芳老师,从心理学角度和我们谈谈如何面对“我们与恶的距离”。
*点击时间码,可直接跳转至王芳老师答问部分
05:26 《我们与恶的距离》,今天为什么仍然让我们回味?
07:31 为什么剧中最后没有告诉我们李晓明行凶的原因?
11:57 分析恶性行凶者的成因,会有“洗地”的嫌疑吗?
17:36 什么是“恶的他者化”?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恶人”?
22:57 男性更容易犯下恶性事件吗?这和“有毒的男子气概”有什么关联吗?
28:24 为什么有人会把刀挥向“无冤无仇的人”?特别是“更弱者”?是想“报复社会”,还是“找存在感”?
对某个群体的仇恨被合理化,是恶性事件更可怕的后果?
32:14 恶性事件罪犯的心理成因有多复杂?什么是日常生活的“危机点”?
41:40 同样经历创伤,为什么有的人会变得更善良,有的人会更相信“丛林法则”?
43:28 精神上的问题和犯罪行为有关联吗?如何理解暗黑人格、反社会人格?
48:20 我们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精神问题?诊断病理,还缺少什么学科的视角?
53:15 在心理危机干预、社会支持系统上,个人和社会还能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修建自己的“安全系统”吗?个人关系世界、社会关系世界存在互相补偿的机制吗?
1:04:03 心理学最近几年渐成显学,为什么让人不安?
1:10:16 NPD、PUA、PTSD…心理学概念的日常化,会助长人们之间的对立吗?普通人如何运用心理学更好地帮助我们?
1:18:45 闲聊开始:平时怎么放松,韩综《思想验证区域》观感…
最后,借用王芳老师的祝福,愿你的身边有光,愿你就是那道光。
本期推荐
王芳 主讲《致独特的你:人格心理学40讲》
本期嘉宾 | 王芳,北师大心理学部教授,看理想主讲人
本期采访、制作 | dy
本期摘录
《我们与恶的距离》每一集最开始那个社会事件,它把更广泛意义上有可能作恶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纳进来了,然后它会去展示可能每一个面向经历的那些创痛也好,挣扎也好,那种人性的摇摆,很细细细密密的展示出来,进而可能就会让你意识到说,原来所谓的罪恶,还有罪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那个人性都是如此的复杂。
/
当一个杀人案发生,你不仅要去关注杀人案本身,更要关注对于方方面面的伤害。于是也就更要回过头去追问——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而不只是说,快点判死刑杀掉就好。以及对于大众来说,如果这已经是一个社会事件了,那么大众是有知情权的。
知道并不等于理解,理解也不等于认同,更不等于支持。如果说了解了成因,就会为犯罪开脱,这太没逻辑了,同时也太看轻——多数人是有基本的道德判断的,以及司法的独立性。
/
所谓“恶的他者化”,也就是说我们会习惯性的把邪恶想象成完全有别于自己的,甚至非同寻常的,很罕见又难以理解的存在。而它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可能会因此而忽略,或者没有办法辨识出,那些其实是在频繁制造邪恶的、也许非常稀松平常的一些环境性的特征。
另外,“恶的他者化”还可能带来一个反向的作用,就是我们把他者视为是邪恶的,并且就只在他者身上看见我们所害怕的东西,那么到头来,所有被我们认作是他者的东西,所有陌生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邪恶的,它就循环上了。
换言之,我们刻意去拉远自己和恶的距离,恶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我们就有可能在未来完全被动的、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猝不及防就会撞上这个恶的随机发生。
反过来,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与恶的距离没有那么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就是一线之隔、触手可及的,那反而就会让我们时刻对潜在的恶是保持警惕的,进而也有可能去做预判和防范。
/
父权制所设定的一整套游戏规则,对男性这个层面的压迫,就是作为一个男性,你需要在一个代表权力和地位的梯子上不断向上攀爬,这样你才是有价值的。但是往上爬也就意味着可能随时失足跌落。于是就要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去维护,或是再去向上争取地位。
比如争名夺利就是一种方式,积攒财富是一种方式,征服女性是一种方式,暴力也是。
暴力也不只有直接的攻击,比如像通过暴力引发了别人对自己的关注,也是一种“地位提升”。
如果我们去看这些人的经历,他们多半都有过社会受挫的经验,而那个挫败的主题,通常都会跟文化当中常见的一些男性主题是有关的,比如说野心、金钱、求偶之类的,而受挫就意味着地位的跌落和失权,意味着自我价值的一种贬低和否定。
那这个时候,“暴力”这种跟男性气质深度捆绑的行为,就会成为一种用以恢复地位、获取自尊,然后同时展示自己所谓“男性气概”的一个方式。
/
那些被伤害的人,从个体层面上来看,好像的确和行凶者无冤无仇,但如果受害者是行凶者所仇恨的“外群体”的一员,比如你是让我遭遇不公对待的那个群体当中的一份子,哪怕这个连接非常牵强,比如说你是那个让我不爽的这个学校里的人,你们其他所有人都是迫害我的当中的一部分,那他的攻击伤害行为也是可以被合理化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行凶者的主观感受上,他认为他伤害的对象并不是完全的“无冤无仇”。
其实这种大规模的行凶或者是暴力的犯罪者,他们往往并不是一时冲动,是有谋划的。他们其实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这些行为是不被法律和道德所允许的,所以他们要给自己找理由,要想办法去解释、甚至美化自己的恶行。而这一部分反而有的时候是会被某些人买单的。
特别是对于外群体的仇恨,当它本身就代表着某种社会情绪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人会为这种极端的暴力拍手叫好,这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部分。
/
国外有一个研究项目,很难得去梳理了这种所谓大规模的攻击者的一些能找到的材料,结果就发现其中有42%的杀手在童年的时候是经历过创伤的,多数是身体暴力或者性虐待,或者目睹过父母自杀,或者是遭遇过严重的校园欺凌;有超过80%的人,大概在事件发生前的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里是达到了一个所谓的危机点,比如说被停职、被解雇,亲密关系破裂,被社会排斥或者陷入个人经济危机等等。
这些危机会引发他们在后续行为上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强烈的焦虑,孤立,然后绝望。他们会感到自己被抛弃了,被羞辱了,被边缘化了,甚至产生自我厌恶。但是这种自我厌恶,最后都外化成了都是别人的错。进而会心怀不满,然后充满了愤怒,紧接着就会开始去策划这种大规模的杀戮。
/
大多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并不暴力,他们甚至更有可能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而不是肇事者。这里我也看过一个数据,说如果一个人患有精神分裂症,那他杀死一个陌生人的可能性只有14.4万分之一。但是我们会看到,好像每当有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听到凶手就是个疯子,肯定有精神病。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说法确实提供了我们对于一件非常出乎意料、不合逻辑、难以理解的事情,这其实是经常陷入一个循环论证——我们先问,这个人为什么做这么可怕的事情,因为他有精神病,那你怎么知道他有精神病呢?因为他做了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
/
有一个理论就讲到,一个人的社会安全系统其实是由两个世界构成的,一个就是个人关系世界,包括比如像我们的伴侣、家人、朋友、关系很好的同事等等,他们可以提供给我们情感连接,以及重要的社会支持。另一个呢,就是社会关系世界,像我们所在的公司,单位,学校,社区,再广大一点,各种社会机构,社会制度乃至整体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稳定程度等等,他们提供给我们经济来源、社会身份、社会保障、社会秩序以及像公平正义这种抽象的道德和价值的依托。
这两个世界其实是有一个相互代偿的关系的,就是任何一个系统失灵,人们就会转而去向另一个去获取必要的安全感。
如果一个人同时对两方面的信任都断裂了,那就很可能会进入一种极度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当中,进而寻求一个极端报复,同时也是在寻求自我毁灭。
/
互助就是最小的系统,我们有时候把“系统”想得太大了,有时两个人之间的那些相互的善意的释放,它就是改变我们两个人实实在在的所处的那个环境和情境的一种方式。
评价...
空空如也
小宇宙热门评论...

ray_4Jfg
7个月前
浙江
10
15:23 老师说得真好:知道并不等于理解,理解并不等于认可,认可也不等于支持。

Citrus_oo
7个月前
新疆
4
感谢分享,让我仔细思考这个社会事件

kiera-z
7个月前
重庆
4
17:36 有报导有社会思考固然会有争议,恶的产生也依然让人痛苦且费解,但是至少比完全无从得知更能疏解大家的无力感。在这里想起了《好东西》中调查记者的陨落的隐喻。

如tu
7个月前
山东
4
31:54 就为了催稿,芳姐的社会心理学,特意发留言

KatherineK
7个月前
江苏
3
挺有意义的一集,如今很多事件一报道,然后就成为了大家表达观点开始争论的工具,很少有集中性探讨思考事件本身及相关背后的问题,一时热度然后就不了了之也没人关心后续

ray_4Jfg
7个月前
浙江
2
58:37 我也好感动。:当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看的时候,能有人把你当人对待。这种善意,我们都需要。

ray_4Jfg
7个月前
浙江
2
1:00:33 我要成为那道光!我就是那道光!

如tu
7个月前
山东
2
Dy啊,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已经在同龄中很成熟了。但在当下,请让我们,庞大的80后人群肯定有,也已经有一些人,他们来自三教九流,内心红黑纠结,有意愿也有能力,如鲁迅先生所说,抗住黑暗的闸门,放更年轻的到光明中去。也许过不了几年,我们会退回黑暗,需要已经全副武装的你们去扛闸门。

如tu
7个月前
山东
2
芳姐和Dy也算是一对神仙cp,不接受反驳。如果质疑,去看看那一期视频。致独特的你,我们何以不同,新书对谈,只有她们俩,精彩,远不止精彩

琅笙
7个月前
宁夏
1
理解人的复杂性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约束之下必然会衍生更多样的观点。
近年来公共舆论场对心理学专业概念和理论的科普固然能够帮助个体理解自我和他人,但更要警惕对专业名词的误用和滥用,要警惕对他者的标签化行为,要警惕社会的医学化导向。
争议引发情绪,情绪带来流量,流量导向利益。所以有必要保护好自己的情绪,别做“模糊的sth/sb”的帮凶。

LovePlato
7个月前
广东
1
视频里提到的ted演讲是这个吗:https://youtube.com/watch?v=qrtIhDaKkwQ

独步91
7个月前
浙江
0
感觉明年恶性事件还会频发的我小板凳坐好了!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恶性事件也频繁发生,然后政府提高底层保障福利,减少贫富差距,媒体宣传愚民娱乐化,男性气质娘化,压制炫富特权信息传播。

旺旺小小酥_Dg8F
7个月前
上海
0
过去其实有段时间媒体热衷详尽挖掘罪犯动机,确实也带来了大量的罪犯崇拜,和模仿犯罪,这也是现在反对过度挖掘的原因。

康康like
7个月前
北京
0
1:04:38 我就是天文的哈哈哈现在还是很小的系

把花鱼
6个月前
山东
0
很有思考意义的问题!

阿汀
6个月前
广东
0
1:02:54 互助就是最小的系统

阿汀
6个月前
广东
0
很有启发,值得重听。

justride
5个月前
广东
0
1:14:53 真好啊,王芳老师。

香蕉鱼的两种生活
4个月前
广东
0
嘉宾好温柔呀,也很有大爱和智慧

香蕉鱼的两种生活
4个月前
广东
0
社会太复杂,个人就只想要简单,捍卫的可能就是个人想要的秩序感🥹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