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沧浪之水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我不知道是改变还是颠覆,只怕我会在接下来的漫长人生中持续而缓慢地意识到,是启蒙、是洞悉人性、是摸索到社会运行的深层机理?还是解开了美好幻象的层层面纱、不再享受单纯且纯粹的快乐、还有做事情的脑回路多长出了一个分支呢?我想我怎么也不会做到书中人物那么圆滑到有些油腻又游刃有余,他们是官场的佼佼者,是玩弄人性的精明之人,毕竟这是一个靠上面人一句话就可以得道高升或者沉寂于世的嵌套结构,洞察人心、眼疾手快、权谋之术、磨平棱角,宦海沉浮的世界莫过于此。雷达曾评价说:读《沧浪之水》,简直有种天机被泄露的感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察觉却又朦胧莫辨的某些东西给挑明了,讳莫如深却又一直有人在暗中操练并受益匪浅的诀窍给洞穿了,这怎不令人豁然复骇然?
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池大为直言劝谏,却因正中要害而被贬出局,在狭窄闭塞的小屋子里过了几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简陋生活,在高人指就点下逐渐开悟,也是无法忍受生活的重压、无法直面自己对于妻儿的愧疚心和羞耻心,无法坦然地面对官高一级压死人的上级,也因落魄没法在同学聚会上体面做人,痛定思痛,彻底荡涤掉了之前那个自我,他热爱抽象的精神道德、素质情操、理想抱负、公平正义,可在现实的种种残酷下他逐渐转变了思维方式,真实是什么?不真实又是什么?位置可以给人带来真实的东西,坚守的某种信念却在现实的淋漓鲜血中显得如此可笑。这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故事,也可以说他磨平了棱角,走上了千百前来早就形成的传统之路,走上了想要生存就要把利益得失放在首位的道路,这个真实的、残酷的、成败论英雄的世界。或许你讨厌的势力之人,有其无路可走的心酸与无奈。

很明显,思路转变过来之后便一路高升,在这个特定的场域中,既经历了空怀壮志、无职无权的苦,也体味了时来运转、有名有利的福,情节构建貌似像本爽文小说。思想未转变之前,池大为活在一种简单的纯粹之中,但固定行成一套规矩还是别用恃才傲物地与之抗衡,前人又不是傻子,血淋淋的现实摆在面前,还不谨以为戒吗?有些人看不惯那些条条框框,期望在大义凛然牺牲之后给后人以启迪,可往往声音各异、众说纷纭,甚至还被扣上沽名钓誉的帽子,这难道不可悲吗?我曾经是漠视规则的人,也不保证以后能否会去除掉潜意识里的叛逆,可是我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我也是没有认识到自己渺小的人,设想过自己傲立在山之巅峰仰天长啸,在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何不快活?可是没有能力和地位的时候,这种少年意气难免耽误了大事,思虑不周和心高气傲的年少的问题,可芳华已逝,便再无年少了,这能承担的起这惨痛的代价呢?那天爸爸水果大亨的朋友送了一箱车厘子和榴莲到家里,我还依稀记得自己被清爽甘甜风味洗胃的快活,由于空间有限,冰箱里的苹果、橘子、辣椒酱被拿了出来,供奉车厘子和榴莲的大驾光临,这就是自我价值,这就是阶层,这就是现实。
不免想起实习时带我的记者老师,曾经年少轻狂,心归四海,背着背包逃课旅行,一个月杳无音信,走遍了南方的山河湖海,坐绿皮火车、住青旅民宿,只因为在图书馆看到了一本书,这是少年意气、是无拘无束、是生活的一万零一种可能性,正当我满怀向往和羡慕的神情注视着眼前这位老师时,他却说到:再也不愿意回去了。不是意气风发不好,不是随性洒脱不好,他早就知道那个年龄阶段的他和他所处的社会群体的身心状态和所思所想,那很美好,很单纯,但是他更爱现在的这种复杂,与其说是复杂,不如说是看透之后再选择简单,或者复杂。凭借着一腔孤勇行事,最后撞个头破血流、落个遍体鳞伤,找谁诉苦去呢?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选择的基础是认知的总和,和一个可以依靠信息推算出的概率性时间,曾经有人跟我说我总爱去尝试小概率的渺茫机会而忽视了大概率的风险性我还不信,实际上凭一腔热血支撑的理想主义就是一捧沙,风一吹,就散了。在隔壁的中文系,因为热爱文学毕业后像当个作家的人不在少数,可这种想法也在现实的面前妥协成了偶尔写写东西放松一下的想法,沈从文先生还在晚年的书籍中写到作家的成功几率如此之小,而仅仅凭借写作来吃饭是如此可笑。(“作者本人居多是无所得的,直到如今为止,能靠出版税收过日子的小说家,不会超过三五位,冰心或茅盾、老舍或丁玲,即或能有点收入,一定都不多”)池大为的空虚之处也在于此,坚持什么,抵抗什么,貌似是永远也想不清楚的答案,大豆绿头先生曾在其豆瓣评论中这样写到:“炎凉冷暖的人情世故里,在波诡云谲的政治舞台中,在光怪陆离的世象百态间,我看到了一个鲜活的人怎么样坚持,坚持到头破血流,坚持到悲哀地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个自觉崇高的坚持里越来越无能为力越来越无法坚持”,然而他的妻子早就认清楚了自己是个俗人,果然还是俗人说话一语中的,略过种种虚幻的抽象概念构建的泡影,直达问题的本质,得到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很多人一语中的说出了问题的本质?就是因为他俗,俗没什么羞耻的,高雅没什么值得标榜的,解决问题的不过都是那些俗物,就是在这煎熬和犹豫中,池大为亲手杀死了之前的自己。
我逐渐发现,脑子的反射弧限定了领悟的局限性,正如我很多话都是后知后觉出现在脑海中才恍然大悟,而这存在的隐患是,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其观念的产物,我爸妈观念一动,家里多了个天天跟我抢牛肉的孩子,千万负债的人的观念一动,世界上少了一个自谋短见的商人,所以在事情发生前,观念已经先行了,做事情是走了一个观念铺就的流程,是践行了那个思维的产物,但是如果这种认知并不真实、并不客观、并不符合规律、并不完善,人怎么会做对事情?也就是说没有这种方法论了然于心,简单纯粹的善意之人也会好人帮倒忙,当内心的声音再瞧不起那些汲汲以求的嘴脸,再看不惯那些虚情假意的讨好时,不妨再想想,存在即合理,他受到过怎样的方法论指导、他有什么深层的诉求,他对面的人是不是也渴望着被尊重和被讨好,他们也许早就知道这是逢场作戏,就像很多时候在外人面前,我需要做的就是一个知书达礼、自信大方的女儿罢了,我不是一个有思想的苇草,不是一个兴致勃勃的小孩子,我是一个群体共识的产物,我是一种现象,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我会设想那个我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自我怎么能就这么轻易改变呢?但最难以捉摸、复杂多端、给人带来痛苦、矛盾与割裂的事物无非是那个自我,哲人说过: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我,你可以说自我是抵挡千军万马的铠甲,但它也是密不透风的围城,万事万物存在个一体两面,无常才是永恒,世界上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变,我的某些观念也应该更加活泛一些才行
另外,书中池大为的上任领导离职之时面临巨大恐慌,自己的意识是否贯彻落实,工作如何展开,自己的地位会不会就无人问津,比给他更痛苦的,是让他失去,多少人一生都在追寻那个我执,而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虚幻意向的填充,没建立起来时,自我便自卑懦弱,建立起来时,自我便无线膨胀,丧失一切时,自我便瞬间崩塌,看不出活着一趟又是为何,看来不同年龄阶段的生存之道各不相同,年轻的热血是勇往直前的号角,中年的成熟是理性审慎的客观需要,晚年很多人修身养性、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寻找信仰。

这本书探讨了很多人性有关的问题,能给人生发出很多感慨与想法,以小说的形式走完一个人的半生,何尝不是一种精彩?以上发言以偏概全,多有纰漏,不过就像池大为心中所想,语言是个辩证法,自圆其说才是硬道理,有时候结论是既定的,观点怎么找也能凑齐个三五个,这么看来心口不一的人可以概括为八面玲珑,但是,这让我们千百年来歌颂的高风亮节和大义凛然的谋臣武将情何以堪?这本书的价值观是一种现实的妥协的总和,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们从小以来接受的教育难道都是假的?我在颠覆中叩问,又不免沉思。论语中的己欲立而立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那些慷慨激昂的铮铮誓言难道都是苟延残喘的逆流言论吗?人无信仰,仅仅苟活吗?可难道不可悲吗?在中华民族存亡之际多少人挺身而出捍卫这寸土地,那英勇无畏的誓言怎么在有些人嘴里就那么不值一提?这就是我们受教育的结果吗?这是前人所希望看到的吗?这是未来的火种吗?有人说利他是理想,利己才是答案,宏大的概念总在被谈论之时溃不成军,可是那些打击的人是真的无奈之举,还是另有所图,还是本身就对于崇高无关痛痒,这还要打个问号,有些概念我还不懂,但有些语句还是像理想之光,照亮去时的道路,鲁迅先生曾说:我们只愿在真理的圣坛之前低头,不愿在一切物质权威之前拜倒。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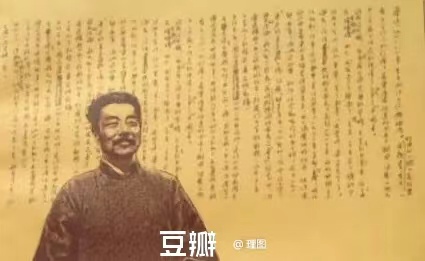
空空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