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是QQ音乐的猜你喜欢最懂我的品味,我妈说我情绪太多了,没人有功夫陪我消化,这么看来随便记点东西是个为人也为己的选择,如果一个小小的备忘录能解决我憋了一肚子的碎碎念,那还需要麻烦别人干什么呢啊?大言不惭地说,最近收到了诸多糖衣炮弹的连续攻击,真不是我社交面广,事实上,我每天都孤独地要炸掉了,天天感慨原来猛兽才是独行,时长唱一曲高歌:我寂寞寂寞就好!然后再轻轻地舔舐自己的情绪波动的额外温存,酝酿成一点点不起眼的文字,貌似还挺有意思的,写着写着就忘掉了一切,忘了自己,也忘了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自己,没错,只有我,举目四望,再无他人,其他人都是陪我玩游戏的NPC,我怎么爽我怎么玩。话说回来还是跟我智障且生来就是天才的舍友胡说八道最有意思,口无遮拦地随地乱吐虎狼之词,这是啥唯我独尊的享受啊,突然发现微服务的花季论坛里那么多生殖知识,看后便爆笑便若有所思,真的巨涨知识,若不是根本没有上过专业的性知识课还有家长一般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对待相关问题,那我们也不会如此好奇以至于在互联网上直接蹦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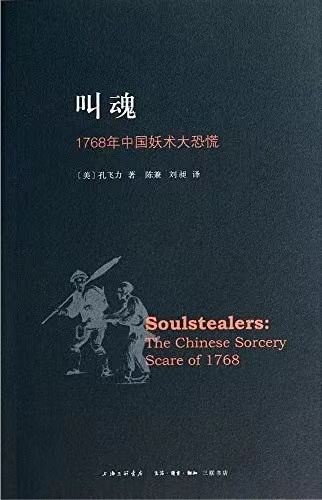
为了参加周一晚上的读书会我正襟危坐严肃认真地看完了这本《叫魂》,一开始还以为是一部讲故事的志怪小说,打算拿出三分随性散漫,三分认真研究,一分精力分给耳机来快速搞完这本书,但是很搞笑的是最后的囫囵吞枣变成了量子波动下啥也没记住的惨状,别说了,原来我才是没有金刚钻偏揽瓷器活的无名小卒,废话怎么这么多!事实上,这是一部体量巨大、论据翔实、耗时五年、被业界奉为圭臬的学术钻研著作,你可以在传播学或者新闻学角度分析它通讯社上传下达的有限性和高效性,也可以在历史研究角度分析它对于史料的选取与分析,当然不排除还有神秘学、志怪说、法学、社会学等等角度都大有分析讨论的空间,阅读《叫魂》成为了一种必备的学术训练,作者利用大量奏折、会典、实录等文献档案对清中页的社会进行了全景式鸟瞰,形成了一部视野恢宏而详实、行文流畅而深入浅出的汉学著作,尽显一派大家学者的独到风范,一开始上任的哈佛校长依旧面临能力不足的非议,但是当此书出世后学术界的全场便鸦雀无声了。

这本书的开头部分便介绍了叫魂案的来龙去脉,起源于一个愚昧无知村民的迷信小事儿,据说依靠打听姓名、剪掉发辫、剪去衣服角等行为便可以剥夺此人的魂魄,但这些案子再怎么荒唐也不过是寻常的治安事件而不会构成全社会的大恐慌,但它为何成为了震惊大半个中国与朝野上下十个多月的叫魂系列案呢?谁是这背后推波助澜的幕后黑手呢?这需要分析社会各阶层的运行状况,孔力飞观察到,普通民众、地方官僚、军机大臣、皇帝对叫魂术的态度是极其不同的。由于没有大型灾荒和自然灾害,商业贸易发达人口数量激增,在作者一针见血的描述下,这是一个镀金的盛世,但是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悬殊、贫富失衡,人民也普遍生活在精打细算和勤奋劳作的边缘线之间,稍不留神就会沦为赤贫,所以就会有人动了巫术妖念的歪心思来坑蒙拐骗,也有人出于排挤流民的念头借巫术实施暴力,由此外乡人面对一定点儿的风吹草动就要联合向衙门举报,政府官僚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一般会选择息事宁人,不要城墙失火殃及池鱼,以此来确保自己的高官厚禄和稳定生活,而当朝廷将此事确立为抬上厅堂的大案时便争相邀功,上下其手,欺骗推诿,甚至出于要制造政绩斐然的假象的考量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每位官员都有自己的小九九,而最高层的乾隆本身呢,也不过是一个系统运行之中的镶了钻的螺丝钉,他在反清覆明的恐怖回忆下居然思危,担心百姓一点点风吹草动演变成的揭竿而起,而这次叫魂案件也给了他一次整顿朝廷、罢免官吏、强化个人权威的机会,最后居朝廷中枢的军机大臣们在保证皇帝面子下不动声色地叫停了案件,由此结束了这场闹剧。当然,作者在后面的章节中重点探讨了满人对汉民的警惕以及传统秦制对自发势力的焦虑合流,还有这背后的官僚君主制度,他这样说到“妖术既是一种权利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一种潜在的权利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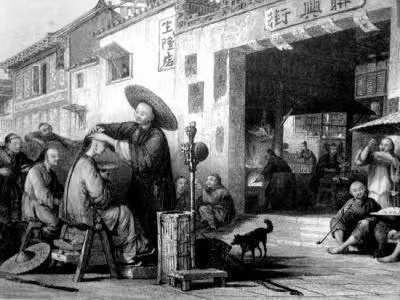
其实你看完还会大概率上认为这是一个中国人完成的著作研究,毕竟这流畅的文笔和详实的文言文引用连中国学者都连连称赞,但是你会发现,作者是费正清的门徒,出生在一个美籍犹太裔的记者家庭。我自己像是一只能接触52HZ的鲸鱼Alice,其他波长的信息均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有办法和更高频率的波长产生强烈共鸣,但是这只鲸鱼却渴望着剖析另一个语言系统,琢磨这种思维方式运行的底层逻辑和成为他的必经之路,啊哈,我又陷入被揠苗助长的斯德哥尔摩症的快乐里了。读书会有一位随机不定时来一口瑞幸咖啡的红头发少女总能和老师保持对话,学理性的分析和简洁的语言令我敬佩万分,而且对比起我起起伏伏跌跌荡荡的情绪波动,她的审慎理性保持冷静客观的处事风格更令我敬佩,我发现敬佩别人的思想产物是我潜意识里一直在做的事情,敬佩是一种礼貌,把这种东西据为己有才是深藏的野心,每当我们提出一些看似很高明很有逻辑很学术化的问题时,骆老师总是用一句这是常识让我们哑口无言,所以如果是常识就不构成问题了吗,常识没有探讨的必要吗,我貌似明白了,我们的不知道的边界仅停留于知道知识本身的层面,而没有思考到要生产知识这一研究问题。这位红头发的女生说:常识是一种包含问题但是没有提出问题的社会共识这句话时,我静下来琢磨了好久。

我还发现老师和学生的思考维度真的差值八百里,他每天都在琢磨新闻学科怎么进行专业化的推进,学术研究如何在保持固有根基上进行进行跨学科交流,还阴阳了一下现在的文科生都不读书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这样会对新闻研究失去本该有的想象力,老师还提到了关于理论的书籍要大量的总体的一并进行阅读,因为各种理论纠葛在一起时研究效果才更为显著,其实,思维的分野也许年少之时就有分叉的端倪,我没有沐浴在资治通鉴的洗礼下而是捧着阿衰和疯了桂宝开心的不亦乐乎,长大后的阅读也只是感到感兴趣的消遣,事实上阅读质量根本就经不起推敲,老师几个问题就给我整的一头雾水,三脸懵逼,他信手捏来的知识量和清晰流畅的语言表达一定是长期阅读和练习训练出来的厚积薄发,我以为的全部其实仅仅是冰山一角,但是遇见大佬对于打击一下自己的嚣张气焰的作用也举足轻重,这让人意识到想要登上学术的殿堂任重而道远。早上醒来的时候CPU已经烧爆表了,一个回笼觉就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一辈子,想到我要往脑子里塞进的知识,往肚子塞进的食物和往生活里塞进的人际关系,我便马不停蹄准备出门了,我在想如何不让自己变成一个连轴转的陀螺或者四处乱飞的无头苍蝇,虽然以前遵从发散性的思维逻辑来践行生活,但是现在我得拿出点针对性来操控我的人生了,不敢做选择说白了还是不勇敢,如果不畏惧那个代价那什么选择不可以为之而奋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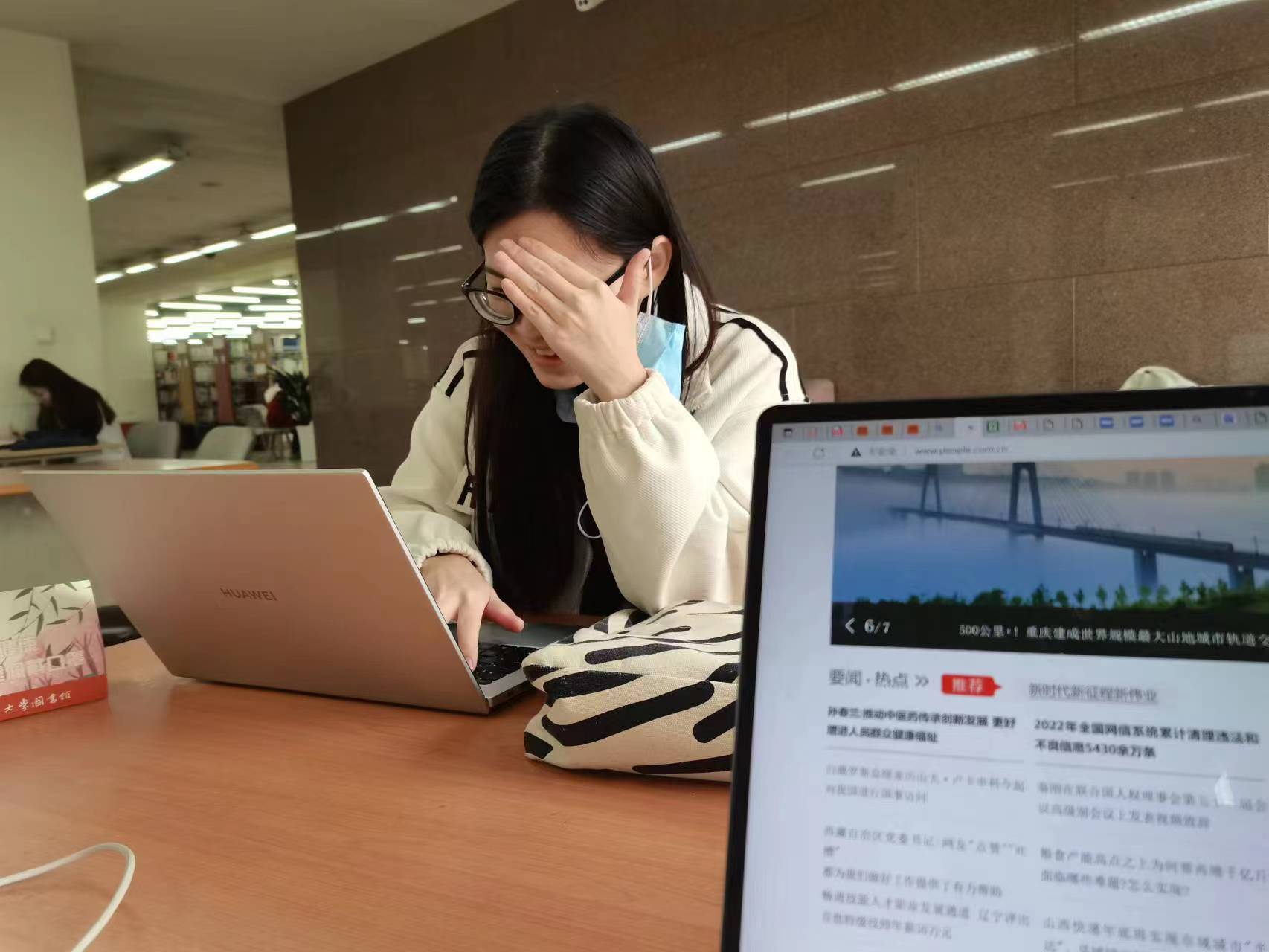
这个女人每天想我想到不可自拔都要专程来看我
空空如也
暂无小宇宙热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