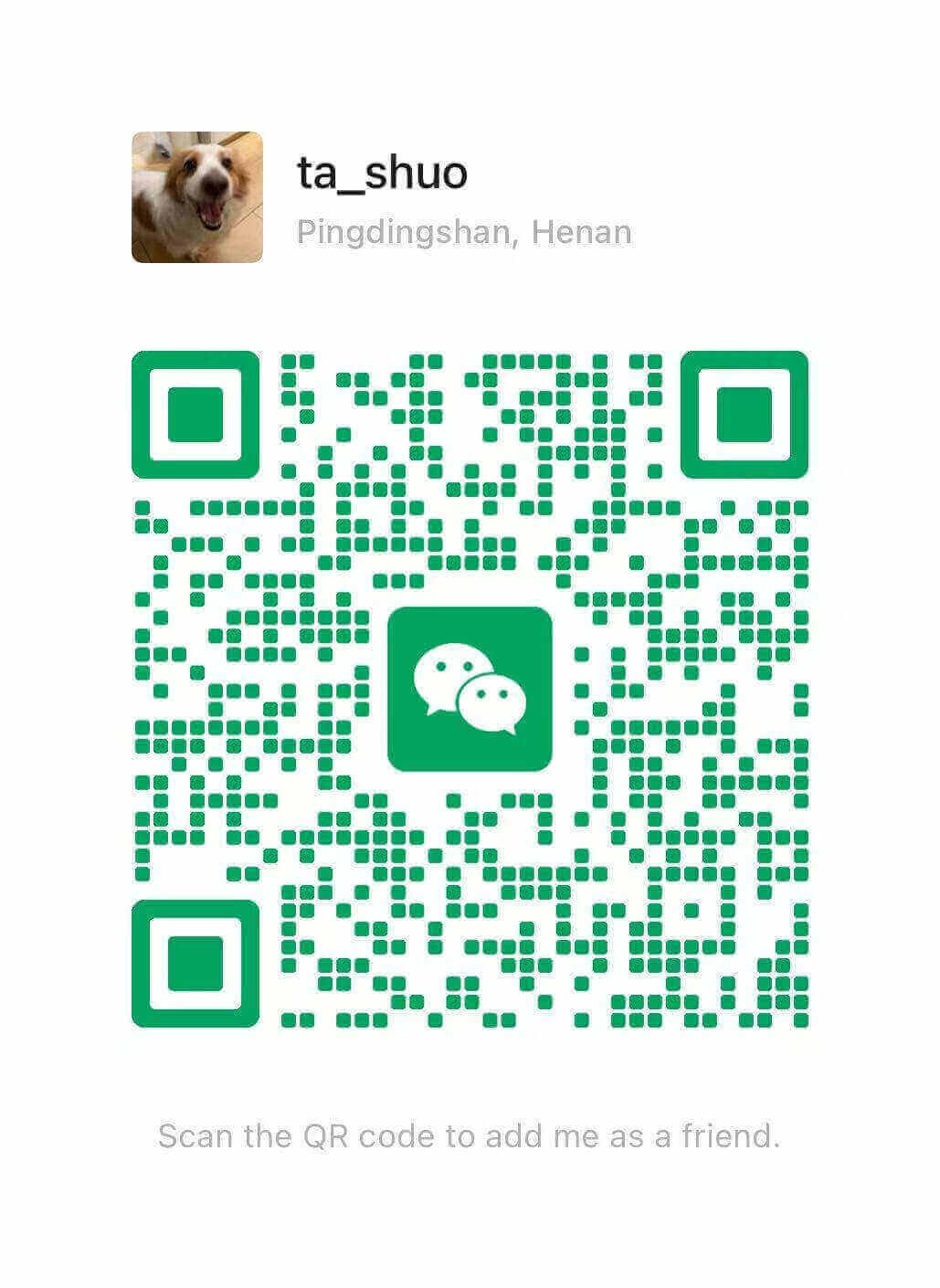你好,或者是你还好吗?今天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当头一棒,原来很多东西的到来不会提前以安抚你的姿态出现,而是杀伐果断地通知你,这让人好不自在。后来我开始思考公平与正义的问题,但因为学时浅薄而毫无头绪,也许需要去认真地读一些书。不过有些事情的出现无非是告诉我这个问题你该体会一下了,别一直当个温室里的小花朵,温室的温暖是因为有壳子罩着,阳光很明媚是因为乌云还没有赶来,所以我想,我坚守的真善美是一种在条件极高的氛围下才可以展现出的现象,在理想化的社会里,善意才会是一种同符合契的选择,而在现实生活中,善意的感染力不敌恶意更具有传染性,正如有句话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后来我哭了,泪水会成为一场预谋,并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盛装出席,不过能哭是一件好事情,这意味着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极致的绝望从来都是无声的,有时候想想,我应该感恩戴德地感受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活,我还有脚可以走路,还有双目可以阅读,还有时间可以纵享孤独,还可以呼吸可以感受露珠,我哪里来的痛苦?我不曾痛苦。再后来我释然了,如果生活已经足够美好,那就要誓死捍卫这份美好,选择善良之人,就不应该动摇自己的价值观,高尚可以包容丑恶,而丑恶却无法理解高尚。不过换言之,这是生存的选择,选择只有不同,没有对错,我能做的就是筛选出我最快乐的一份天地,这是我不为人知的秘密基地,只要有了这个地方,我便可以接受那些价值观割裂的瞬间,毕竟这不曾成为也不会成为我的课题。以上是我为自己的妥协所做的辩护,这份辩护让我自洽,让我不至于把污浊咽下喉咙,这套说辞就像是安置在思想里的空气净化器,即便雾霾会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它也会加足马力,从不畏惧。

之后我带着降噪耳机在学校里步履匆匆,要去忙着解决心头若有若无的焦虑,可是我抬头看见了嬉笑的情侣,潺潺的小溪和皎洁的月光,我意识到,也许我走路的速度太快了,快到要惊扰这一树的寂静。然后我把自己放置在河边、放置在泥泞的小径、放置在潮湿的雾色、放置在深夜中仿佛静止的时间里,我好像感知不到了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在这个夜晚静止了,那天我的朋友跟我说,时间是拍打着沙滩的海浪,它从来都不是线性生长的,它时常回旋、或者跌落,就像是她爱读的普鲁斯特,人们会在作者的文字中感受这种时间的折叠。我觉得十分深奥,她的话像是劈开海浪的光束,给我狭隘的思维打开了一簇神经突触,后来我一直在不知不觉中体味这些文字,今天漫步在四下无人的夜晚,我在黑夜中看不到周围的人,在雨后的世界里看不到白日的躁动,我突然感受到了那种时间的静止,我四散飘飞的思绪也静止了,恍惚间,我被镶嵌在了一段时间的缝隙里。后来回到座椅前,我写下了莫名其妙的文字,不明觉厉的情绪,和无病呻吟的伤感。我记录这脑袋里的感受,这种通感的体验是我忘乎所以的娱乐。我在想,对于任务来说,我知道我为什么选择拖延了,也许在我心中的价值排位来看,我在做我当下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就像我厌恶程序、叛逆规则、无视条例一样,这没什么好炫耀的,但也没什么好自责的,按照地图一板一眼的行走你会抵达达早已筹划好的目标,可是如果你贪玩跑去了野花遍地的岔路,你也许会误入爱丽丝的兔子洞,邂逅一场曼妙无比的梦境,我想,选择做梦还是选择清醒,这都不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既然每辆列车的目的地都是尘土,那为何不好好看看这路上的风景?

下面是我奇奇怪怪的胡言乱语,它不会体现出任何被逻辑修理过的痕迹,不过我想这就是它的魅力。
时间从来都不是一个表盘上的数字,你相信吗?扎加耶夫斯基在诗中写到:“我的半天过去了,有一天半个世纪也会这么过去。”
二零一三年第九个星期日的傍晚七点四十七分,在钟摆声消失后,时间就静止在你的瞳孔里,不曾流淌,人在静止中沉睡,在沉睡中藏匿,在藏匿中停止存在。又或许是从未存在。静止是一种去惊悚化的枪,没有人会质疑它的杀伤力,事实上你很清楚,它会在任何一个一个瞬间扼杀住你羸弱的身躯,却迟迟不肯开枪。你在静止中感到令人羞耻的恐惧。也许你怕的不是时间刻度的停滞,而是潮落之后与岁月的离别,当你开口说话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头顶已然是三十年后的一轮月圆。

我被黑夜吸引,路边枯萎的草是西班牙的寡妇,四下无人的夜,寂静的雨,婆娑朦胧的雾霭,替我挡住了世界的喧嚣,我从未觉得我原来如此不需要热闹。音乐会与你成为唯一的朋友,事实上,耳中是另一种狂欢--鼓点密集、情绪跌宕、人却飘飘然,物非物、人非人,大雨瓢泼后的夜可以萃取出悲伤,伸出舌头,也能品尝到黑色的快乐。黑色一直都被误解为一朵忧郁的云,可是,在你没发现的角落里,它默默地舔舐着草儿被光刺痛的双眸,在你脚步无法触达的小径,它漂浮在溪水膨胀的清冽中,躲藏在被遗弃的废旧烟盒里,黑色是一段被催眠的长镜头,一首卖弄迂回技巧的散文诗,一行欲言又止的稚气未脱的省略号。举目瞭望,我一不小心就撞见了曾经无数次在同一时空埋葬的自己,她与人貌合神离,那个同行的人,是日后渐行渐远的灵魂,他们谈论着一切,却从来都是自说自话。她是卑劣的、自惭形秽的、黯然神伤的;他是无知的、冷漠的、自以为是的。她是畏惧的、进退维谷的、情非得已的;他是迷茫的、不知所措的、自欺欺人的。她一边慢条斯理一边歇斯底里,他一边无动于衷一边错愕惊恐。他们所向往的永恒,其实剥开来看,一半是速朽。他们不懂速朽,只知道这样下去会让人枯萎,而枯萎是虚无的前奏,虚无是年少时一种过于廉价的煽情游戏。

存在是种幻象,逃离存在才是归途,风停止后,她是一根孤独的松鼠的绒毛,坠落到潮湿粘腻的土壤中,放肆地朝着灭绝狂奔而去。她醒过吗?我想从未吧,夜晚的人不会撒谎,痛苦的橡树叶不会怀疑,但凡是苏醒的意识悄然生长,她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浓郁的恨意,一种从心底酝酿然后弥散到脸庞的情绪,她也许会朝着那个迷失在泡影中的眼神大骂一句,去他妈的,谁赐予你的软弱,你又为什么拿这东西当成唯一的盾牌?原来我是那么憎恨曾经的软弱,捎带手也恨起来现在的怯懦。不勇敢的原因还是从未坚强过,不曾坚信过,没错,质疑是杯35度的酒,不够消毒,不够解忧,没办法消愁,只会让模糊的丑陋更加丑陋。我想,如果明天醒来是河边的一棵小草,就纵享风雨飘摇,不用担心大树的事情,植物的欲望就是没有欲望。如果明天醒来是一座山,就俯视这世间蝇营狗苟的人类,别质疑别人阐述的尊重,你生来就注定是高不可攀的顶峰。她以为这就是注定的生活,注定的人,以为这是百年一遇的命中注定,可笑的是,她从来都不曾考虑过自己,她试图倾诉却放弃,试图表达却哽咽,试图移开挡在灵魂里的冰山,却发现北方凌冽的寒风已经孕育出了漫天鹅毛大雪,试图奔涌出烧灼滚烫的岩浆,却发现荒山扩散的野火已经将遍地野草蹂躏殆尽,最后选择留给自己一厢情愿的知难而退,作为潦草的谢幕。也许她和他从来都不是同一束玫瑰上的尖刺,只是看起来生出了一些毫无瓜葛的菱角而已。熟睡中,她变成一株捕蝇草的时候,他是一朵郁金香。也许她应该果决一点,在转瞬即逝的美好前充满敬畏,为防止爱恋受到时间的腐蚀,在发现破绽之时,就要像厌恶泥沼一样厌恶珍珠,像吹灭蜡烛一样吹散迷雾。不过话说回来,也许当你知道它会阖然长逝后,你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坚定。

在更晚的夜晚,我看到一首诗,诗中这样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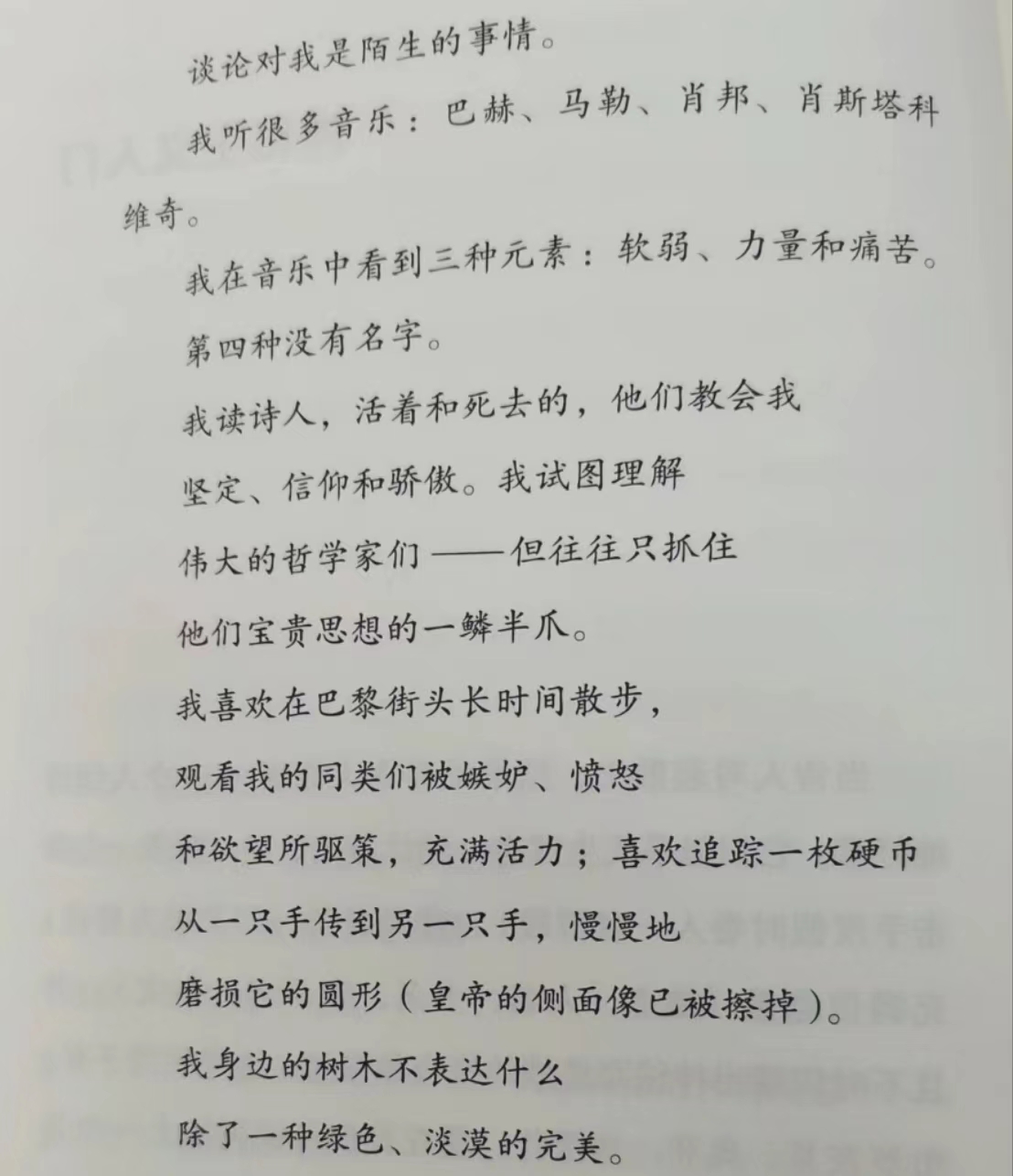
空空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