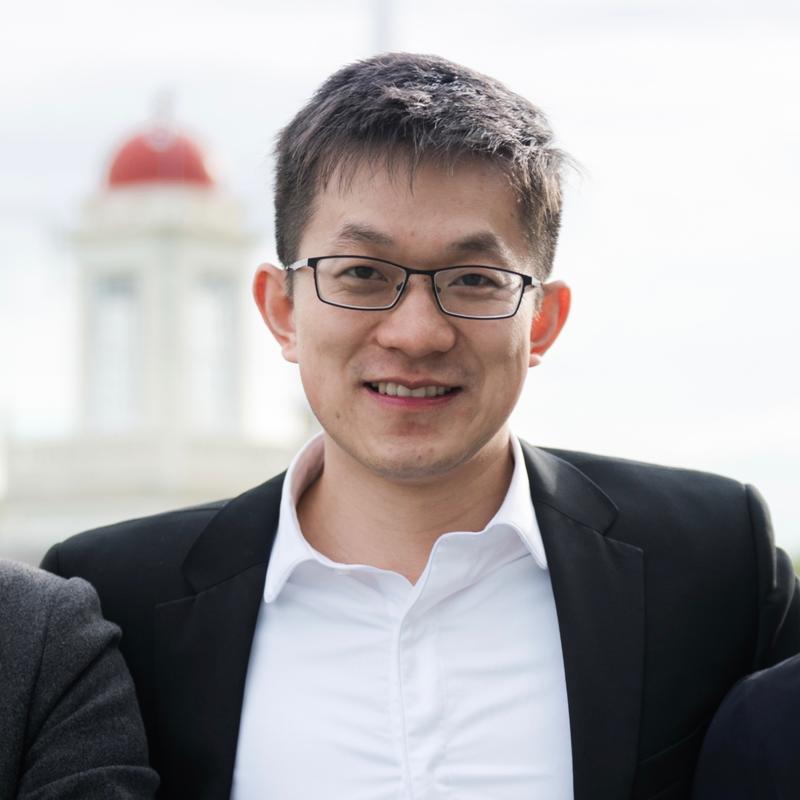
完成统一后,秦帝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法治化。其中土地私有制 在底层群众中认可度高。而这些被剥夺权利的前朝王室贵族,反而成了统一后的主要矛盾。如何消化这些还尚存实力的组织机构是摆在帝国面前最大的政治难题。为了化解阶级矛盾和地域观念差异,帝国将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标准化工具推广至全国适用。但起初效果不明显而且阻力很大。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帝国的官僚人才数量不能满足全国的需求。被“地域习惯和观念”拖了后退的秦帝国,组织了一场关于是开倒车选择封建制 还是 继续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的学术讨论,目的是通过辩论,吸纳和启用更多官僚人才。我们之前讲过,在战国后期的学子中,许多人才是法道共鸣的技术派、具有法家思想的儒家务实派。
帝国是希望这些务实有才干的人进入帝国官僚体系,帮助帝国决定坚定不移的推行郡县制。无论是孔子的儒家学说还是被道家追封的老子学说,在经过200年的传承后,难免因为学生的资质不同,使原来的学说变质变味。刚建立的统一帝国把最贴近学说原版的典籍收归国家,并禁止民间私藏诸子书籍;这一行为同时也是为了快速推进文字的统一。对待还抱守旧观念的六国遗民,秦人一直是用猛药的,哪怕是对待自己。虽然惩罚私自藏书的行为,但相比于违背其他秦法,发配充军进行思想改造已经是比较轻的惩罚了。至于所谓坑杀的“儒生”也是对另一事件“的移花接木。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与打仗取得天下不同 治理国家对当政者的心智、体力、意志力要求极高。统一六国已经消耗了始皇帝太多的精力,而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需要他付出更多的心力和体力。从自然中寻找养生力量的方士,开始聚集在皇帝身边提供功能性的药物。方士门凑在一起从老子的道德经和上古医书中寻找 线索并且奉为理论。当始皇帝发现自己被骗后,对这些人士进行了全面的封杀。一部分逃往深山避难的方士利用道士的身份做保护,在底层社会层面继续着他们的谋生之道,包括但不限于求仙问道 化学-药品实验 以及医学探索。至于后世史书将这些零碎的背景拼凑成“焚书坑儒”的政治事件,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汉王朝的需要,毕竟,刘邦被封“关中王”后继承了秦帝国的关中地区,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对秦帝国法治社会的认同度极高。这种继任者对前朝泼脏水的事件,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当然,汉帝国对道士团体的政治纵容与偏爱,也会引发一场政治灾难,我们之后会讲到。
回到秦帝国这边,由于扶苏和楚系的关系,始皇帝在生命弥留之际将皇位传给了胡亥;扶苏调往北方抵抗匈奴,这说明两个问题:
1.秦帝国皇储数量和质量都堪忧;
2.帝国军队面临着南北东西多线作战的巨大压力。
如何同化原六国败者!?—吕不韦试图用传统和观念,始皇帝选择编户齐名的法治,但他两都忽视了败者需要被尊重的最后一丝底线。
帝国在与六国的征伐中还都属于光明正大的阵地战,而统一后,当这些贵族反叛势力转入秘密组织时,更容易组织起底层群众进行破坏。帝国军队面对移动战和分布式地下战的成本过高。
秦国此时需要的不仅仅是官僚人才,还需要降低治理旧观念的成本。当政治治理时间不足时,官僚阶级会简化流程,让更多年轻人充当劳役,以此降低社会管理成本。这也给历史记录留下了,秦政残暴的口实。
李斯此时也已经70多岁,体力,心智,勇气,魄力,都不再是一个政治敏感的政治家。帝国在始皇帝去世后留下了许多问题。包括土地私有制带来的新旧阶级矛盾、旧思想的卷土重来、匈奴的军事压力、官僚管理制度的不完善,社会生活层面的不稳定,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帝国的行政成本支出过高,缺少了始皇帝的支持,英雄迟暮的丞相李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实力来消化帝国面临的政治难题。
此时帝国又犯了另一个错误就是剥夺了军人从军的荣誉感。统一前秦国军人对国家的认同,就是每个个体在战斗中拼劲全力的意义。而此时,北境游牧部族的压力,帝国简单化的将兵役、力役、罪犯都送往北方边境,而延误兵役的罪罚是最重的。这种军人的荣誉感使命感,随着兵源素质底下被稀释。为日后陈胜吴广的起义埋下了伏笔。
亡秦必楚口号的真实性,我们尚且未知,但作为号召力,其效果确实被试图
张扬楚国的起义军陈胜吴广 所利用,各地流民武装和民兵团体纷纷利用起这句口号 作为各自复仇的正当性。刘邦和项羽也是其中的一员。项燕的“末世论”般的口号,帮助各反叛势力以最低成本的达成目标共识。项羽是江苏宿迁人;刘邦是江苏徐州丰县人,是吴国地区的人。这些人自来楚国的边缘地区,受楚文化或者利益影响都不大,却都用上了“亡秦必楚”的口号,快速的完成了组织搭建;另一方面,吴地的地理环境和生存压力,会在秦之后的历史上随着地理开发扮演更重要的作用。
空空如也
暂无小宇宙热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