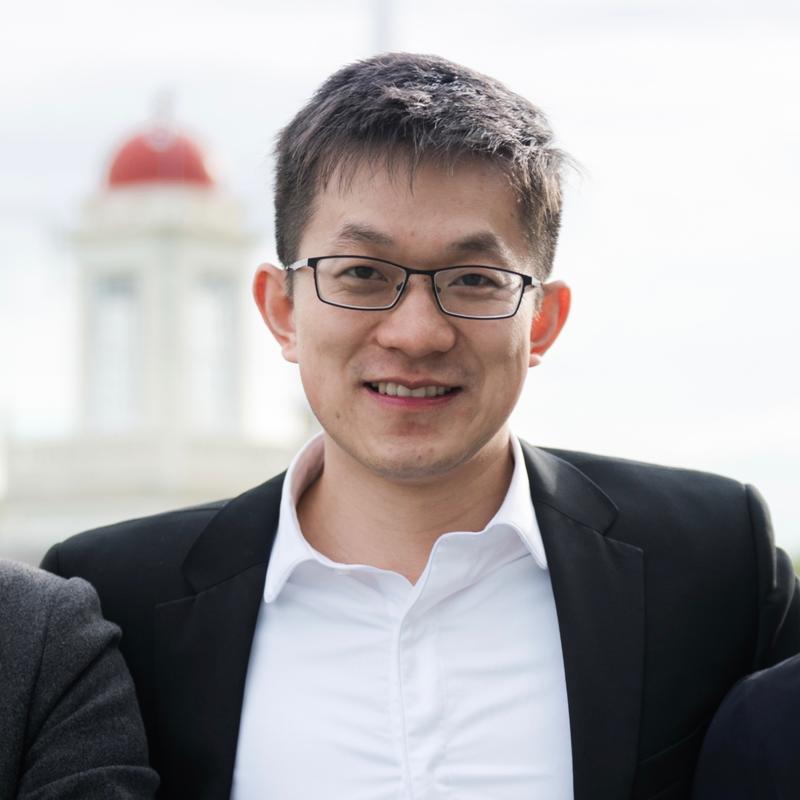
文景之治的本质是在 将皇权向上集中的过程中, 避免政治精英内部斗争的消耗。当异性诸侯被刘姓诸侯渐渐取代后,汉朝进入了王权与诸侯惜昔相印”的稳定时期。文静之治时期国家多次免税,减免地租,荒地复耕,人口增加,社会活力得到一定的恢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其实,此时的税收政策是非常被动的,因为土地免税和收税的区别不大。由于诸侯分封制 对王朝的税收-财政体系造成威胁。土地和人丁税收是封地自治的——这导致中央财政税收的兑现度低。所以文景时期,国家将国有土地、荒地大量分配给农民,允许农民私自拥有这些土地,而这些土地的税收直归中央。这些农民是中国最早的自由农,与秦帝国靠军功得到的私有土地的制度相比,这种土地私有制更普及。到汉武帝早期,这种“为国兴力,还利于民”的政策依旧持续普惠到很多的老百姓,自由农的数量依旧在增长。社会活力不断被释放。
汉初的法道共治,行政管理成本较低,汉王朝主要的财政压力来自于边关的防守支出。秦汉政权的更替,匈奴趁机做大。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反侵扰,以绝后患,而这需要皇帝有集中权力来调动资源和征兵。汉武帝政府针对现状需要“精准”实施政策来收回王权:
1. 在土地政策方面 实行 推恩令稀释诸侯财产的集中度,削弱诸侯的经济和税收的自主权。
2. 行政管理方面:设中朝尚书令归属少府管理,少府是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的职能机构。加强尚书令,是为了制约宰相的权力,将财政权收回中央政府。这也佐证了文景时期税收兑现度低。
3. 资源调配方面:官方垄断必要盐铁等资源的供销,经济运行规律中那只看不见的手要被看见。保证了在扩大疆土、抵抗匈奴的战争财政需要。
在加强王权的时候,董仲舒前瞻到“农民利益与中央财政利益绑定过于直接,中央收回权利的过程势必会与农民阶层发生矛盾,如果此时贸然使用法家制度来处理矛盾,容易走上秦帝国的老路“。为了减轻中央与农民的直接矛盾,董仲舒开始有意培养官僚阶级来作为中央与地方执行过程中的矛盾缓冲带。
尊儒便是政治管理的主动选择,董仲舒如此这般的宣扬儒家,说明儒生官僚集团还未大量的进入政府中枢。他将“三纲五常”的伦理观融入儒家的政治学理念中,为之后的汉王朝吸纳并培养了积极出世又稳定的行政管理人才。秦帝国的经验告诉后世官僚集团的管理成本是远远低于血亲和贵族的成本的。!!!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 儒林列传》记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从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出“焚诗书与坑术士“,是两件事件。术士是炼丹的方士也并未儒家。并且这两件事和六艺从此缺焉,并不构成因果逻辑关系。
此时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渲染,可以为儒家获得一种被残暴欺压的受害者形象,有助于推动儒生为汉帝国做事的忠诚,并且后世证明。这一行为的成功。
《汉书·董仲舒传》中对遵儒术原因的记载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熄灭,然后统纪可一 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尊儒“是“坑儒“的另一种极端的表达,两种运动的出发点一致,均是为了构建
”唯一的依据标准“,但造成的社会影也全然不同。“尊儒”的结果带来了权力结构自上而下的稳定。“尊法”带来的是自下而上的法理标准化。所以,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则是实行“外儒内法”儒强法弱,的治国路线。
到汉武帝初期,在中国统一的疆土上,帝国有了稳定的官僚阶级,中央可以不用简单粗暴地“重农抑商”的阻止跨地域性的贸易。平原-中原-草原的社会活力再次被激活。在军事层面,汉武帝以陇西郡为支点,向西增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打通河西走廊地带。公元前60年,汉朝在河西走廊地区接连设置了军事情报机构。并在乌垒城(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的轮台县)设立西域都护府。汉王朝至此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央帝国形态。在行政和军事的双重保护下,新开发疆土上的“贸易“逐渐兴旺起来,这就是后来被我们称为丝绸之路的商贸道路。秦汉时期,社会层面建立起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之外的信任——这就是,贸易契约的信任,这种信任以交易体验为主,成为跨地域、跨民族的共识。
空空如也
暂无小宇宙热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