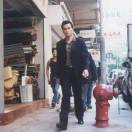简介...
本期主播:许宸/赵大宝/艾晶/方舟
嘉宾:刘昊
00:25 请叫我们预言家
09:31 Mandarin 还是很可惜
31:25 说好的读编往来!
45:37 一个没法复述的抽象问题
55:05 乐夏遗珠大盘点
#节目介绍
The Bootleg Podcast 不赖电台,由“靴子腿一号二号成员”许宸和赵大宝创立。大家可以在小宇宙电台、网易云音乐、蜻蜓FM、苹果 Podcast 和喜马拉雅 等平台搜索收听。
#联系我们
微博:@赵大宝 @许宸xuch
评价...
空空如也
小宇宙热门评论...

躲藏的鼻哥窿
4年前
3
給各位主播送上中秋寫下的一些關於自己音樂習慣養成的回憶,感謝你們在過去三個月的陪伴,讓我每週都有所期待和思考,謝謝艾晶,謝謝許宸,謝謝方舟,謝謝大寶: 80年代,中山紀念堂,蓓蕾劇院,交響樂團,第一次聽到小提琴的聲音。我沒聽懂台上很嚴肅的大家在表達什麼意思,但是腦海裡面記住了那個扇形的音樂大廳和安靜的觀眾,紅色綢緞沈重下垂的幕布。後來爸問我想不想學拉小提琴,五歲的我似是而非地點了頭,開始了學琴的經歷。琴弦和琴弓,在有限的時間裡面,都是製造了各種噪音和不安,甚至琴譜架被重新裝置成架子鼓,各種鍋碗瓢破被筷子敲打,小提琴並沒有奏出過被期待的聲音,但卻因此打通了音樂想像力和思考。
80年代,靠近窗台那有一個1米多高的木衣櫃,左邊是拉的抽屜,有4層。左邊是一個拉門的衣櫥,我很喜歡打開右邊的門,讚進去,躲在掛著的衣服裡面,聞著木頭和衣服乾淨的味道,儘管裡面漆黑一片。這衣櫃上面曾經放著一台三洋品牌的收音機,可以同時放兩盤磁帶。那時候聽得最多是AM頻道,可以聽到香港的,甚至台灣的電台。爸擰開清晨『18樓c座』各位街坊的嬉笑怒罵,催促那個依然貪睡的小孩。盛夏午後的涼風,和著林子祥的『亞里巴巴』急速的音韻,睜眼看到淨是窗外的樹影婆娑 。 後來的電台都變成了FM,本地的電台頻道越來越多,慶幸的是他們大多都還是延續著香港電台的風格,晨早的『18樓c座』從此變成了『一盅兩件』,各種家長里短的街坊事,伴隨著是每天的刷牙洗臉,穿衣收拾,一起奔向校門。
90年代,戴上第一台隨身聽耳機,第一次感受到立體聲的震撼。沒多久,家裡添置了最重量級的設備,一台帶擴音器的音響套裝,左右兩個木製大音箱,粗壯的音源線,帶著冷光顯示的索尼CD播放器和一張張在街邊掏回來的打口CD,青春期自此有了足球以外的新夥伴。爸用來試音的萬寶路進行曲,經常被我濫用成大鳴大放,讓那個小小的空間如同巨大的衝擊波,震盪著那窄窄的窗框和無比冰冷的防盜網。BlueNote的爵士,Pet shop boy的電子,Radiohead的迷幻,Nirvana的絕望,混合著各種成長家庭中的野蠻,橫衝直撞。
在音樂的養成史中,有著反叛,對抗,妥協和思量。以為俗不可耐的南泥灣,卻在後來成為個性中細膩的溫床。生命或許漫長,但獨留音樂的哺餵卻如此短暫。謝謝這些被注入成長的滋養,至少可以讓我變得和別人不太一樣。

赵大卫宝爷
4年前
3
谢谢一直关注和留言啊!音乐多好,能串起来这么多事情!

HD231790e
4年前
3
对于“客观”,我个人的理解是各种主观的最大公约数。

DizZZZ
4年前
3
我是三天前听完了不赖的本期更新,然后刚刚看完了德夏大结局。关于刘昊说起德夏那段谈谈我的一点看法:不说有的人拿德夏当标准攻击别人这个事(我几乎不刷社交媒体也不关心这些),就说德夏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节目的打分走向这点。为什么,德夏,能造成,这样的影响?为什么不是不赖电台或者其他的评论乐夏的节目呢?我觉得这事值得想想。
第一次接触德夏时并不感冒,当时感觉他们由于文化差异get不到一些中国的情感背景。渐渐发现Julian和Max具有超强的感受力和敏锐洞察力。即使完全不懂歌词的情况下也能准确表达出这个歌哪儿好,或者描述出这个歌里的情感。我做为一个普通观众,看乐评类的节目的一个预期就是期望,host能用他的描述,准确捕捉到我心里那个感受到了但表达不好的东西。也就是共鸣与共情所产生的愉悦感。我记得前几期不赖超级碰瓷儿里方舟就有过这种“精准击中“的表达,听到时就想拍巴掌,“说得太好了!”那种。而大宝常常能提供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不了解也想不到的那种,从而实现“信息获取”的愉悦。同时呢,大宝以他的包容和对谈话节奏的掌握成为四个人不同观点的粘合剂,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节目都是赵大宝在的那些期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德夏的四个人吸引人的一个点就是他们既有音乐人的身份,同时又有置身圈外的距离感。(更何况Julian和Max都有各自可爱的点,“可爱”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品质——这扯远了。)我想说的是,观众会认为他们的节目有料,同时又没有那种“我听某某多年/我认识XX多年”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由此我想回来,不赖电台的核是什么。这可能是许辰和赵大宝也在探索的事。在结束了与方舟和艾谁谁的联合唠嗑之后,一个开放性的选择又出现在眼前了。我的思考结论是:要有自己的料。拿“天才捕手计划”举个例子,他们的节目请来各个行业里的人讲述他们的职业故事,这是有自己的料。那么靴子腿一号二号是否可以以音乐行业从业者的身份,聊一些行业之外的人不可能聊的内容,或许是一种选择。如今播客、vlog茫茫多,聊科幻的,聊游戏的,聊电影的,聊啥的都有,但凡聊的好的,基本都是在某一领域浸淫多年,有积累的东西。
我一时兴起胡逼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写得也不怎么好。但是我相信一点:胡逼说也总比沉默要好。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年纪,沉默往往已成习惯。

泡芙_0dNQ
1年前
上海
3
回来连听了第二季你们所有节目

myhardcandy
4年前
1
唯一的遗憾就是在最后的遗珠推荐乐队名单里,一支重型乐队都没有,哪怕核都没有……(当然也理解几位的音乐偏好,只是略表遗憾)

HD231790e
4年前
0
德夏那段,同意。尤其是max的立场是非常明显的,我也会看德夏,用来跟国内以及自己的音乐欣赏倾向进行比较。但也确实看到有人引德夏来反驳他人观点,感觉挺别扭。

KuKuCA
4年前
0
谢谢,听了每一期

TbeAcolDUO
4年前
0
以后见

bingx
4年前
0
德夏看着就是图一高兴。拿他们乐迷个人的观点来怼国内乐队,吃饱了撑的。

TbeAcolDUO
4年前
0
我也想看后摇!

TbeAcolDUO
4年前
0
今年我还以为会有 发光曲线毕竟有歌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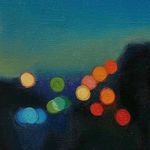
小二灰
4年前
0
28:08 听到昊哥看德国小伙上了头,我自己心里都莫名难受,谁能心平气和地听着自己生出来的孩子被人骂,甚至误读呢?
说得真不算多,问题是,在这个以快为主流的时代,踏踏实实听播客,再静下来想想的人,真不多。
感谢这个节目陪我度过了一个个的骑车上下班时间,甚至会趁着红灯暂停再往前倒重新听的那种。感谢你们。

何足道_ZdEF
4个月前
湖南
0
这期感觉都高了,哈哈,有意思?